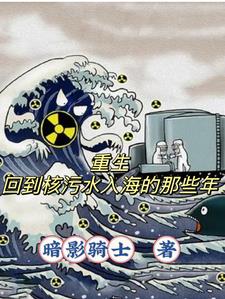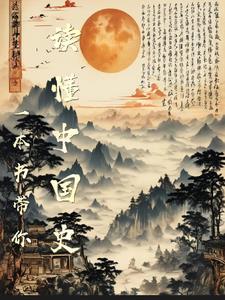第十八章 宋高宗南渡:偏安一隅,重建宋廷
102-1162年间,南方人口从约1000万增至1600万,北方则从约1000万降至600万(扣除战争损失)。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力:占城稻(早熟、耐旱)从福建推广至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逐渐形成;纺织业方面,苏州的“宋锦”、杭州的“缭绫”成为贡品;制瓷业则以龙泉窑、景德镇窑为代表,产品远销海外。
临安的经济地位尤为突出。作为“行在”,临安人口超百万(《梦粱录》载“诸色杂卖”中“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成为“东南财赋地”的核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1142年南宋财政收入为4500万贯,其中江南东路、两浙路占比超60%。为支撑财政,南宋政府完善了赋税制度:除“两税”外,增设“经制钱”(附加税)、“和买”(政府预购丝帛)等,形成多元财政体系。
3.4 文化认同的重塑:“华夏”正统的延续
南宋的文化成就,本质上是“华夏正统”的重构与升华。
理学(道学)的兴起是文化重建的核心。朱熹、陆九渊等学者通过“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建构,将“忠君爱国”与“文化道统”绑定。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强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这种思想将政权合法性从“血缘”提升至“道统”,为南宋提供了哲学支撑。
文学与艺术则展现了多元性与韧性。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怆,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豪迈,共同塑造了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健,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婉约,则融合了南北文化的精华。《武林旧事》载临安“诸色杂卖”中,“书肆”林立,“士大夫家藏书万卷者往往有之”,可见文化之盛。
四、历史评价:偏安的局限性与文明的延续
4.1 “偏安”的双重性:生存智慧与历史遗憾
南宋的“偏安”常被批评为“苟且”,但其背后实则是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从政治看,通过“行在”仪式与礼制延续,南宋保住了“华夏正统”的法统;从经济看,南方经济的开发使王朝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撑;从文化看,理学的兴起与文学艺术的繁荣,塑造了独特的“宋韵文化”。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之伟大处,正在其能于乱世中保持生机,于破碎中寻求完整。”(《国史大纲》)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暗影骑士)的经典小说:《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522322字09-17
- 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凝香笔)的经典小说:《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最新章节全文...
- 1821613字06-26
- 穿书师尊是个大反派
- 2926577字04-29
- 卡牌:重塑天地规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马铃薯三岁了)的经典小说:《卡牌:重塑天地规则》最新章节...
- 1308066字06-10
- 御鬼者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沙之愚者)的经典小说:《御鬼者传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3193750字06-25
- 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粨月)的经典小说:《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最新章节...
- 753612字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