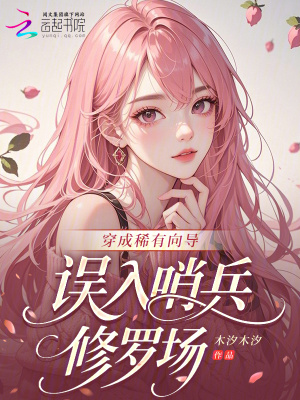第十六章 党争之祸乱局:派系倾轧,朝纲不振
。但随着党争加剧,这些政策或被废除(如元佑更化),或被滥用(如绍圣绍述时期“青苗法”强制摊派)。
元佑年间(1086-1094),全国耕地面积较熙宁年间(1068-1077)减少15%,粮食产量下降20%;到哲宗末年(1100年),财政赤字已达“岁入之半”,不得不加征“经制钱”“总制钱”等苛捐杂税(每贯税钱增加20-30文)。《宋史·食货志》记载:“民力既殚,而国用愈不足,于是始有经制、总制之名。”百姓因赋税过重,“卖田鬻子,流离道路”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军事:战略摇摆,边防崩溃
北宋的军事积弱,与党争密切相关。对西夏战争中,新党主张“积极防御”(如王安石支持“熙河开边”,收复河湟地区,切断西夏右臂),旧党则要求“弃地求和”(如司马光主张“弃熙河,还西夏”)。政策反复导致宋军“进无寸功,退失要地”:1099年,西夏攻占宋军坚守三年的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宋军损失数万人;1100年,哲宗亲政后虽试图反击,但因旧党官员掣肘,“将帅不得专其权”,最终无功而返。
对辽战争中,党争同样误国。哲宗亲政后,新党为扭转“元佑更化”的软弱形象,贸然发动“元符北伐”(1100年),却因准备不足(军队缺乏训练、粮草未备)惨败,宋军“十丧三四”,被迫签订“屈野河之盟”,割让河曲之地。徽宗时期,新党余脉蔡京集团为巩固权力,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1120年),约定联合灭辽后分取燕云十六州。然而,北宋军队因长期党争已不堪一击,1125年金军南下时,“汴京守军不满七万,老弱占半”,最终酿成“靖康之变”的惨祸。
五、历史的镜鉴:党争的教训与反思
北宋党争的悲剧,本质是制度缺陷与人性的双重失败。其教训对后世极具警示意义:
(一)制度约束: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虽先进,却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皇帝的“人治”倾向(如神宗偏袒王安石、哲宗纵容章惇),使党争失去了制度性的平衡机制。现代政治中,“权力制衡”仍是避免派系倾轧的关键——无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都需有独立的监督机制,防止任何一方权力过大。
(二)政治包容:超越“非黑即白”的对立
北宋党争的激化,源于士大夫将“政见分歧”异化为“道德审判”。真正的政治文明,应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通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网游之九转轮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莫若梦兮)的经典小说:《网游之九转轮回》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21899938字07-14
- 智械之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夏玉月)的经典小说:《智械之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830855字10-28
- 译电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灯轻剑斩黄泉)的经典小说:《译电者》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328375字07-26
- 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UG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凤今天不想码字)的经典小说:《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
- 994528字10-01
- 黑暗本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番石榴爵)的经典小说:《黑暗本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85452字06-26
- 穿成稀有向导,误入哨兵修罗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木汐木汐)的经典小说:《穿成稀有向导,误入哨兵修罗场》最新...
- 318250字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