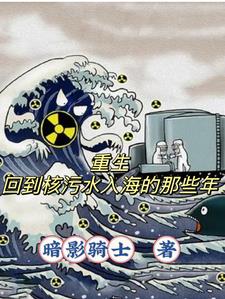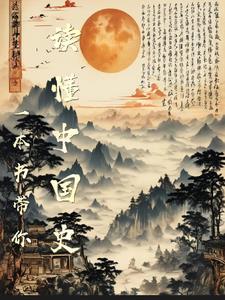第十六章 党争之祸乱局:派系倾轧,朝纲不振
混乱。苏轼曾在《论给田募役状》中批评程颐“专务虚名,不务实效”,程颐则反讥苏轼“轻薄无行,好为讥讽”。
哲宗亲政后(1093年起),为扭转“元佑更化”的颓势,起用章惇等新党,发起“绍圣绍述”,全面恢复新法并报复旧党: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今海南),司马光被追夺谥号,旧党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章惇甚至提出“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连高太后垂帘时颁布的“免行钱”(减少官员特权)也被废除。
至此,北宋党争彻底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政策随皇帝与权臣的更替反复摇摆,官员因站队不同而命运骤变,朝堂之上“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宋史·奸臣传》感慨:“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而党祸益烈。”
四、党争的破坏:朝纲不振与国势衰微
持续百年的党争,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最终加速了“靖康之变”的到来。
(一)政治:行政效率瘫痪,信任体系崩塌
党争导致朝廷决策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一项政策出台前,需经反复争论;推行中,又因反对派阻挠而扭曲变形。例如,王安石的“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价(由官府在丰年收购粮食,灾年平价出售),却因新旧党争被曲解为“与民争利”——反对派攻击“市易务”(管理市易法的机构)“贱籴贵粜,渔夺民利”,最终迫使朝廷于元佑元年(1086年)废除“市易法”,导致粮价暴涨,百姓“饿殍遍野”。
更严重的是,官员的晋升与贬谪不再基于政绩,而取决于“站队”:支持新法者即使无能也能升迁,反对新法者即便贤能也被打压。例如,元佑年间(1086-1094),旧党官员刘挚因反对章惇被贬为“鼎州团练副使”,而新党官员吕惠卿(曾因“华亭案”被弹劾)却因支持章惇官至宰相。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使北宋官场充斥投机取巧之辈,真正有能力的“能吏”(如李纲、宗泽)反遭排挤。
(二)经济:改革成果付东流,民生陷入困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新法的许多措施本可缓解“三冗”危机: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剥削(据统计,熙宁年间民间借贷利率从30%降至10%),募役法减轻了农民负担(原来需服差役的农民每年可节省3-5个月的劳动时间),市易法稳定了市场物价(熙宁十年,汴京粮价较景德年间下降15%)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暗影骑士)的经典小说:《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522322字09-17
- 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凝香笔)的经典小说:《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最新章节全文...
- 1821613字06-26
- 卡牌:重塑天地规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马铃薯三岁了)的经典小说:《卡牌:重塑天地规则》最新章节...
- 1308066字06-10
- 穿书师尊是个大反派
- 2926577字04-29
- 御鬼者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沙之愚者)的经典小说:《御鬼者传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3193750字06-25
- 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粨月)的经典小说:《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最新章节...
- 753612字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