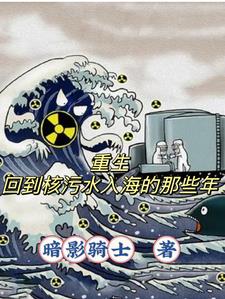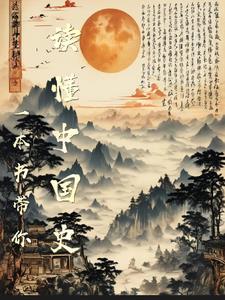第十五章 北宋文化昌盛:诗词璀璨,科技辉煌
道并重”:“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反对西昆体的浮靡,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其《食糟民》写道:“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以直白的笔触揭露官府盘剥农民的弊端,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实践。
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梅尧臣、苏舜钦,则致力于诗歌的“平淡美”。梅尧臣提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其《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以朴素语言描绘山间景色,看似平淡,却余韵悠长。这种风格影响了后来的王安石、黄庭坚,成为北宋诗歌的重要审美取向。
如果说诗文的革新是“破旧立新”,那么柳永对词的改造则是“开疆拓土”。柳永早年科举失意,长期流连市井,熟悉民间音乐。他将晚唐五代的小令扩展为慢词(长调),以铺叙手法展开叙事,用市井语言描写市井生活。其《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铺陈杭州的富庶;《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将离别的愁绪写得缠绵悱恻。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柳永的词,让文人词从“案头”走向“市井”,从“雅玩”变为“大众娱乐”。
(三)后期:豪放与婉约的双峰并峙
北宋后期,诗词的发展呈现出“双峰并峙”的格局:一边是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以“以诗为词”的气魄突破音律束缚;另一边是婉约派集大成,以细腻的情感刻画登峰造极。
苏轼是北宋文化的“通才”,其诗词更是“豪放派”的标杆。他提出“词别是一家”,却主张“以诗为词”——将诗的题材、意境、手法引入词中。《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个人壮志与宇宙时空结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将哲理思考融入中秋赏月,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理性精神。王国维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苏轼的“旷”,正是北宋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写照。
婉约派的代表,则是秦观、周邦彦与李清照。秦观的《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以牛郎织女的故事写爱情,突破了传统“悲离伤别”的套路,赋予爱情以哲学高度;周邦彦精通音律,其《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以工笔描绘离别场景,结构严谨,音韵和谐,被称为“词家之冠”;而李清照的出现,则将婉约词推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暗影骑士)的经典小说:《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522322字09-17
- 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凝香笔)的经典小说:《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最新章节全文...
- 1821613字06-26
- 卡牌:重塑天地规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马铃薯三岁了)的经典小说:《卡牌:重塑天地规则》最新章节...
- 1308066字06-10
- 穿书师尊是个大反派
- 2926577字04-29
- 御鬼者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沙之愚者)的经典小说:《御鬼者传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3193750字06-25
- 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粨月)的经典小说:《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最新章节...
- 753612字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