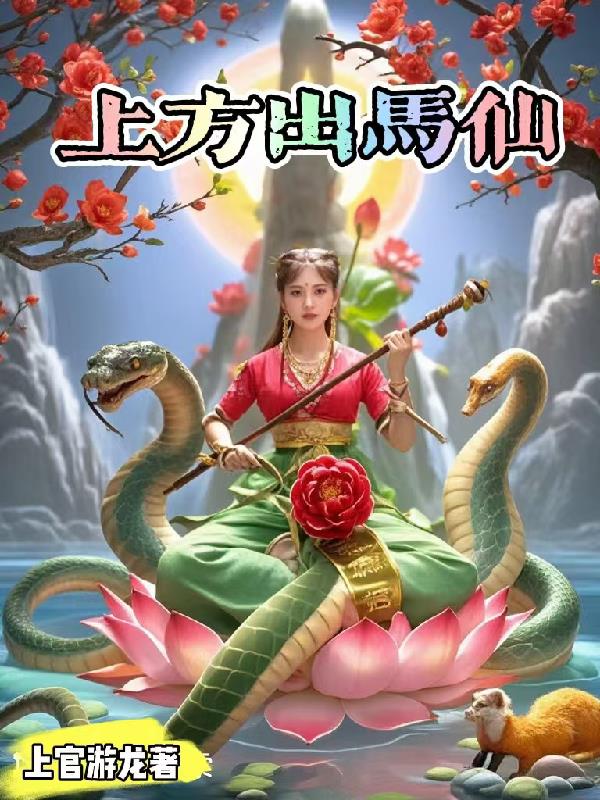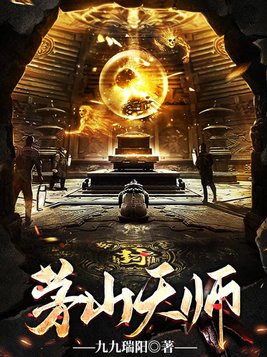第1640章 无畏擒龙(45)
狗剩早跑了,肉都凉在碗里。”
砚之咬排骨时,肉香混着骨髓的浓在舌尖炸开,突然看见陶罐底的青花图案——是株结果的腊梅,枝桠上挂着个小小的纱袋,和花架上的一模一样。原来这院里的每个物件,都在悄悄呼应,像群默契的演员,在时光的舞台上共演着一出长戏。
下午,砚之帮着老人给青果松绑,纱袋已经勒出浅浅的痕,像给果实系了个永久的信物。“再过十天就能摘了,”老人用软尺量着果围,刻度停在“三寸一分”,比预想的大了些,“你祖父说‘饱满的果子得有点勒痕,才显得实在’。”
砚之摸着果皮下的勒痕,突然想起昨天给葡萄剪枝时,发现藤条上缠着片绣品碎布,上面的腊梅图案已经被阳光晒得褪色,却依然能看出是阿婉的针脚。“这是植物在收信物,”老人把碎布埋进土里,刚好在腊梅根旁,“你给它什么,它就收着什么,比人诚实。”
那天傍晚,砚之在样书的后记里补写:“植物的记忆藏在年轮里,人的牵挂刻在勒痕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印记,其实都是时光留下的邮戳。”她写这句话时,窗外的青果突然抖了抖,纱袋在风中轻轻摇晃,像在为文字点头。
夜里起了风,葡萄藤的叶子被吹得哗哗响,像谁在院里翻着本厚重的书。砚之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老人在院里走动的声音,时而有竹片加固花架的闷响,时而有棉布擦拭样书的沙沙声,像首温柔的夜曲,在月色里轻轻流淌。
天快亮时,砚之被露水打湿的窗纸惊醒,推窗时看见青果的橙黄又深了些,像块被月光镀了层金的玉。老人正往花架旁的土里埋着草木灰,灰白色的粉末落在青石板上,像撒了把碎雪。“这是最后一道工序,”老人用竹耙把灰耙匀,“能让果子更甜,就像给故事加个圆满的句号。”
砚之蹲下去闻草木灰的味道,烟火气里混着泥土的腥,像把岁月的味道揉在了一起。她突然明白为什么老人总说“万物相生”,那些藏在草木灰里的智慧,那些落在松绑时的分寸,那些渗进文字里的留白,其实都是时光教会的平衡——恰到好处的给予,才是最长久的守护。
那天上午,村里的老银匠来了,背着个黑布包,包上别着枚银质的腊梅果,是用去年的果子翻模做的,纹路里还沾着些铜绿。“我来给果子打个银托,”老银匠掏出工具时,砚之看见他的镊子上缠着红绳,和阿婉的线是同批,“等摘下来能当摆件,也算给张老先生(指砚之的祖父)留个念想。”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上方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上官游龙)的经典小说:《上方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115886字07-21
- 茅山天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九瑞阳)的经典小说:《茅山天师》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166967字07-21
- 和豪门大小 姐分手后_一只花夹子【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和豪门大小 姐分手后》作者:一只花夹子【完结】文案:【原...
- 620878字09-09
- 江医生今天追回宋老师了吗_真是兔了【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江医生今天追回宋老师了吗gl》作者:真是兔了【完结】文案...
- 855093字09-09
- 杀出狂人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大雨滂沱行)的经典小说:《杀出狂人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914129字12-20
- 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修)的经典小说:《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最新章...
- 6453499字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