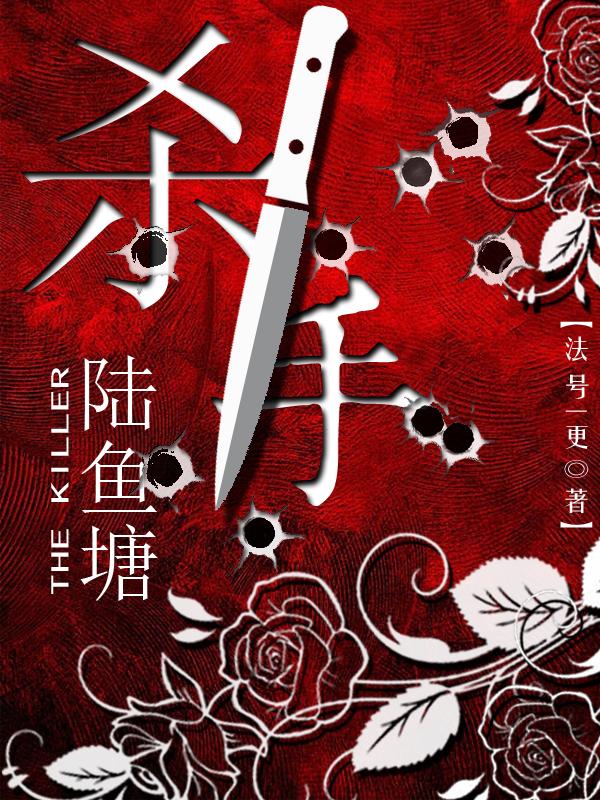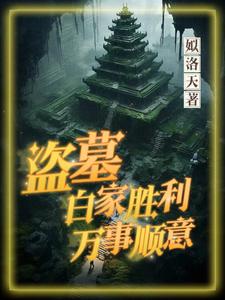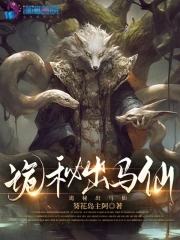第1637章 无畏擒龙(42)
风过时哗啦啦地响,像串会唱歌的风铃。“等腊梅结果了,”老人的目光落在摇曳的碎布上,“就用这些布做个锦囊,把果子装进去,算是给你祖父的回信。”
砚之看着那些彩色的碎布在风中舞蹈,突然明白为什么老人总说“静远堂的故事不是我们的,是大家的”。那些看似散落的片段——阿婉的绣品、祖父的书稿、孩子们的碎布、鸟妈妈的羽毛,其实都在时光里慢慢织成张网,把所有的思念和牵挂都网在里面,长成了最温暖的模样。
中午,老木匠送来个新做的书架,紫檀木的,香气混着桂花香漫了满院。书架的隔板上刻着许多小小的凹槽,每个槽里都嵌着片腊梅花瓣,是用树脂封的,像把整个春天都锁在了木头里。“我爹说这叫‘暗香藏’,”老木匠擦着额头的汗,“当年他给阿婉姑娘做首饰盒,也是这么嵌花瓣的,说‘看不见的香,才最让人念想’。”
砚之帮着把祖父的书稿摆上书架,发现每个凹槽的位置都刚好对着书脊上的书名,《北地草木记》对着片含苞的,《静远堂札记》对着片盛开的,像老人在给书籍配插图,让文字和花朵在时光里相依相伴。
下午,砚之在书稿里写下:“真正的传承,不是把故事锁在箱底,是让它像院里的草木,在风里、雨里、孩子们的笑声里,慢慢生长,长出新的枝桠,开出新的花。”她写这句话时,钢笔突然漏了滴墨水,在纸上晕开个小小的圆,像祖父在为她画句号,又像在为新的故事画起点。
傍晚时,老人开始做桂花糕,石臼里的糯米被捶得发出咚咚的响,混着孩子们的笑声,像支古老的歌谣。他往米粉里撒着桂花,动作均匀得像在播种,每粒桂花落下时,都在粉里留下个小小的印记,像时光的印章。“你祖父说做糕得顺时针揉,”老人的手掌在粉团上打转,“说‘顺着自然的劲,才不费劲’。”
砚之坐在旁边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两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像幅晃动的皮影戏。她突然发现灶膛的角落里藏着根炭笔,是祖父的,笔杆上刻着个极小的“远”字,和书稿上的签名一模一样。原来祖父的气息,早就钻进了这院的每个角落,在烟火里,在草木里,在老人的动作里,从未散去。
夜色渐浓时,鸟妈妈飞回来了,嘴里衔着条小小的虫子,落在腊梅苗上,警觉地看了看四周,才跳进窝里。孩子们屏住呼吸,像在观看场神圣的仪式,直到鸟妈妈喂完雏鸟,展翅飞向夜空,才爆发出一阵欢呼,惊得葡萄藤上的露珠簌簌落下,像撒了把碎银。
砚之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
-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这崽也太好带了叭[...
- 458890字09-25
- 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修)的经典小说:《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最新章...
- 6453499字05-09
- 时空长河的旅者
- 2757038字12-01
- 杀手陆鱼塘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法号一更)的经典小说:《杀手陆鱼塘》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431517字12-24
- 盗墓:白家胜利,万事顺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姒洛天)的经典小说:《盗墓:白家胜利,万事顺意》最新章节全...
- 14587370字07-01
- 诡秘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葵花岛主阿)的经典小说:《诡秘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023251字12-25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http://www.qibaxs7.com/modules/article/images/nocov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