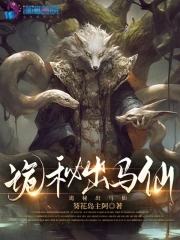第1637章 无畏擒龙(42)
音,时而有竹片敲击花架的脆响,时而有塑料布摩擦的沙沙声,像首守护的歌谣,在风雨里轻轻哼唱。
天快亮时,雨终于停了。砚之跑到院里,看见花架被吹得歪向一边,老人正用竹竿把它顶直,他的蓝布衫已经湿透,贴在背上显出嶙峋的骨感,却像株老松,在晨光里挺得笔直。“苗没事,”老人往花架下垫着石块,声音里带着些微的喘,“就是土被冲掉了些,得补上。”
砚之蹲下去扶苗时,发现根部的土壤里露出个小小的东西,是枚银质的梅花扣,想必是阿婉的绣品散落的,被雨水冲了出来。她把梅花扣埋回土里,刚好在根须的上方,像给种子系了个小小的信物,让它知道,有人在土里守着它的过往。
那天上午,砚之在书稿里写下:“风雨中的守护,是最沉默的承诺,不必说出口,却比任何誓言都坚定。”她写这句话时,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纸上,把字迹镀上了层金边,像祖父在为她的文字盖章。
中午,村里的老中医来了,背着个蓝布药箱,药箱的提手上缠着圈红绳,是李婶新换的。“我来给张老先生把把脉,”老中医的手指搭在老人的手腕上,眼睛却盯着花架上的腊梅苗,“这苗长得精神,比去年的枸杞旺多了。”
老人笑着递过杯桂花茶:“托你的福,去年的枸杞泡酒,现在还香着呢。”
“那是你用了心,”老中医的指尖在老人的脉门上轻轻点着,“养植物跟养人一样,得顺着性子来,急不得。你看这苗,知道往有光的地方长,多聪明。”
砚之看着两人说话,突然发现老中医的药箱里露出半截书稿,是她前几天借给李婶看的,上面还贴着片桂花做的书签。原来这院里的故事,早就走出了静远堂的墙,像株蔓延的葡萄藤,枝枝蔓蔓都缠着村里人的生活,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串成了珍珠。
下午,砚之帮着老人翻晒藏书,在《北地草木记》的夹层里发现张火车票,是四十多年前从漠河到杭州的,座位号是“13”,和砚之来静远堂时的座位号一模一样。“他总说这号码吉利,”老人把火车票夹进砚台的盒子里,“说‘13’像棵长歪的树,看着不直,却有韧劲,能扛住风雨。”
砚之摸着泛黄的火车票,想象着祖父当年坐在火车上的样子,窗外的风雪呼啸而过,他的怀里却揣着包腊梅籽,像揣着整个春天的希望。原来有些旅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归宿,就像这张车票,兜兜转转,终究要回到静远堂的土里。
傍晚时,老人开始酿桂花酒,新采的桂花铺在竹匾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师妹你冷静点儿_这名字好【完结+番外】
- ( 内容简介: [百合] 《师妹你冷静点儿! gl》作者:这名字好【完结+番外】文案:...
- 226558字09-09
- 九公主的心尖宠_嗔墨【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九公主的心尖宠》作者:嗔墨【完结】简介:文国的纨绔子弟...
- 872662字09-09
- 就算是治愈系也要上战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冬瓜是瓜)的经典小说:《就算是治愈系也要上战场》最新章节...
- 608032字11-20
- 【星际】夏虫观其不语冰
- 【星际】夏虫观其不语冰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星际】夏虫观其不语冰》情节跌宕起...
- 107693字09-15
- 龙傲天今天被哥哥洗脑了吗
- 990002字09-27
- 诡秘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葵花岛主阿)的经典小说:《诡秘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023251字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