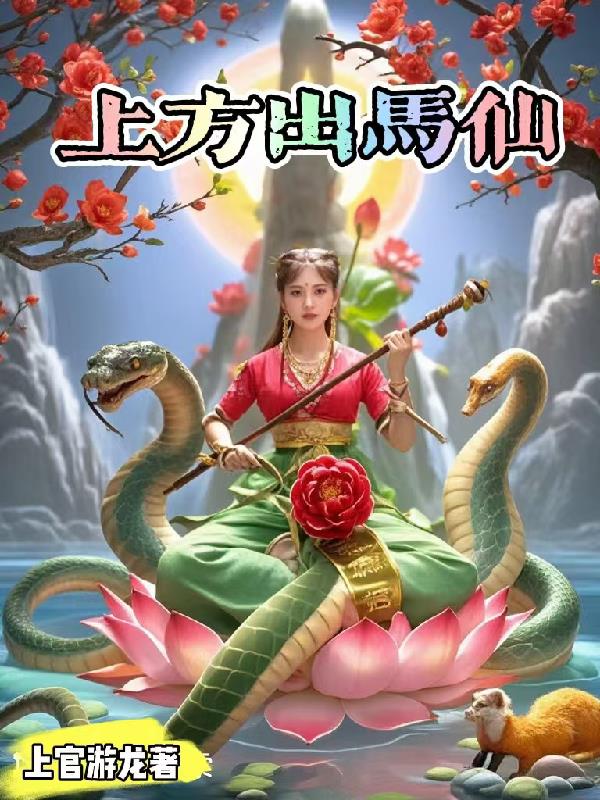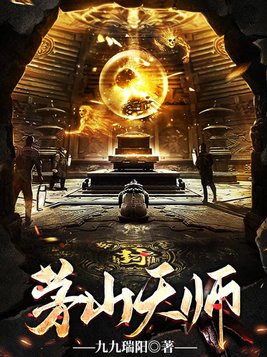第1637章 无畏擒龙(42)
砚之在静远堂住到第九十天的时候,腊梅苗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高,枝桠上抽出了七片叶子,最顶端的那片新叶卷着,像只攥紧的小拳头。她用老人给的竹尺量苗高时,发现土壤表面多了些细密的裂纹,像谁用指尖在土里画了张网。“这是根在往下扎,”老人端着个陶瓮从井边回来,瓮里的水晃出细碎的光,“得浇点淘米水,去年的葡萄就是这么喂壮的。”
砚之接过陶瓮,手腕的红绳浸了水,颜色深得像块玛瑙。她往花架前蹲时,看见青石板上有串小小的脚印,是村里的孩子留下的,脚印尽头有片被踩扁的桂花,黄色的碎瓣粘在石缝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盘。“他们总爱来看苗,”老人用竹片把桂花扫到树根下,“昨天小石头说要给苗唱童谣,说‘唱歌能长得快’。”
那天上午,县里的文化馆来人了,扛着摄像机在院里转来转去,镜头从腊梅苗扫到葡萄架,从老人的银发扫到砚之的书稿,最后停在东厢房的书架上。“我们要做个‘乡村记忆’系列纪录片,”戴眼镜的年轻人递过来杯绿茶,茶杯上的图案是株腊梅,和阿婉绣品上的如出一辙,“李婶说静远堂藏着半个村子的故事,得好好拍拍。”
老人坐在竹椅上接受采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补丁,那是用阿婉留下的蓝布补的,针脚细密得像蛛网。“没什么好说的,”他看着镜头时,眼尾的皱纹像被风吹过的水纹,“就是些种树、看书的日子,跟院里的草木一样,枯了又荣,荣了又枯。”
砚之蹲在花架前整理书稿,摄像机的嗡鸣声里,突然听见老人提到祖父:“他写东西时爱啃笔头,钢笔帽上总有牙印,我说‘文人的斯文呢’,他说‘这样思路才顺,像给笔喂了食’。”砚之摸着自己的钢笔帽,果然有圈浅浅的凹痕,是这些天写稿时不知不觉啃出来的,原来有些习惯,真的会隔着时光遗传。
中午吃饭时,李婶带来笼蟹黄汤包,褶子捏得像朵盛开的菊花。“我娘说这包得趁热吃,”李婶用竹筷夹起个汤包,汤汁在薄皮里晃悠,像装了整个秋天的鲜,“当年张老先生(指砚之的祖父)最爱这口,每次来都要吃两笼,说‘南方的精致,全在这一口鲜里’。”
老人往砚之碗里放了个汤包,醋碟里的姜丝切得极细,像撒了把碎金。“你祖父吃汤包总烫嘴,”老人的筷子碰了碰醋碟,发出清脆的响,“我说‘慢点吃没人抢’,他说‘好滋味就得趁热,凉了就失了魂’。”
砚之咬开汤包的一角,鲜美的汤汁在舌尖炸开,混着姜丝的辣,像把整个江南的秋天都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上方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上官游龙)的经典小说:《上方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115886字07-21
- 和豪门大小 姐分手后_一只花夹子【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和豪门大小 姐分手后》作者:一只花夹子【完结】文案:【原...
- 620878字09-09
- 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修)的经典小说:《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最新章...
- 6453499字05-09
- 茅山天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九瑞阳)的经典小说:《茅山天师》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166967字07-21
- 我女友是侦探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萧梨花)的经典小说:《我女友是侦探》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101913字07-28
- 江医生今天追回宋老师了吗_真是兔了【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江医生今天追回宋老师了吗gl》作者:真是兔了【完结】文案...
- 855093字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