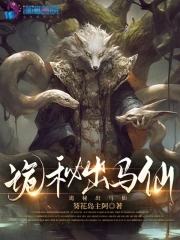第1636章 无畏擒龙(41)
的绣品。老人从西厢房的樟木箱里翻出个蓝布包,里面裹着几十块绣片,有的是未完成的腊梅,有的是刚起针的桂花,最上面的一块绣着两个小人,坐在银杏树下分食桂花糕,衣襟上的盘扣是用银线绣的,闪着温润的光。
“这是阿婉最后绣的东西,”老人的指尖拂过小人的眉眼,那里的丝线已经有些褪色,“她病着的时候说,要把咱们仨的样子绣下来,等冬天没事做了,就拿出来看看,像又在一起过日子。”
砚之的手指碰到绣片边缘的流苏,是用许多细股丝线拧成的,和竹篮提手上的红绳如出一辙。她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祖父总爱用红绳给她扎辫子,说“女孩子的头发得用点颜色衬着,才显得精神”,那时她不懂,现在看着这满箱的绣品,才明白有些牵挂会变成习惯,藏在最寻常的日子里。
傍晚的风带着凉意,砚之坐在东厢房续写书稿。她写阿婉的绣针如何在布上跳舞,写老人的竹篮如何盛着新采的桂花,写祖父的钢笔如何在稿纸上流淌,写这三样东西如何在时光里交织,像三条缠绕的藤,最终长成一棵茂盛的树。
写到一半时,她听见院里传来轻微的响动,探头出去,看见老人正往玻璃罩里喷水。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和花架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像幅被拉长的水墨画。水珠落在嫩苗上,折射出七彩的光,像谁在绿尖上挂了串小小的彩虹。
“你祖父说,”老人见她探头,转身时带起的风拂动了檐角的铜铃,“植物和人一样,得常看常护,不能等出了问题才着急。就像写故事,得每天都琢磨着,不然思路会生。”
砚之回到书桌前,发现稿纸上落了片桂花,是从窗外飘进来的。她把花瓣夹进书稿,突然想起祖父夹在《北地草木记》里的银杏叶,原来这些不经意的收藏,都是时光留下的书签,标记着那些值得记住的瞬间。
夜里,砚之被雷声惊醒。她跑到院里时,看见老人正用塑料布遮盖花架,雨珠顺着他的银发往下淌,在下巴尖汇成细流。“别怕,”老人见她站在廊下发抖,把身上的蓑衣披在她肩上,“这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正好给嫩苗冲冲土。”
砚之披着蓑衣站在雨里,闻到蓑衣上淡淡的桐油味,混着雨水的腥气,像回到了祖父的书斋。她突然想起书斋里的那盆文竹,总是摆在朝南的窗台上,祖父说“植物得跟着太阳走,人也一样,得朝着亮处活”。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雨停时,天边泛起鱼肚白。砚之帮着把塑料布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师妹你冷静点儿_这名字好【完结+番外】
- ( 内容简介: [百合] 《师妹你冷静点儿! gl》作者:这名字好【完结+番外】文案:...
- 226558字09-09
- 九公主的心尖宠_嗔墨【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九公主的心尖宠》作者:嗔墨【完结】简介:文国的纨绔子弟...
- 872662字09-09
- 就算是治愈系也要上战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冬瓜是瓜)的经典小说:《就算是治愈系也要上战场》最新章节...
- 608032字11-20
- 【星际】夏虫观其不语冰
- 【星际】夏虫观其不语冰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星际】夏虫观其不语冰》情节跌宕起...
- 107693字09-15
- 龙傲天今天被哥哥洗脑了吗
- 990002字09-27
- 诡秘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葵花岛主阿)的经典小说:《诡秘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023251字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