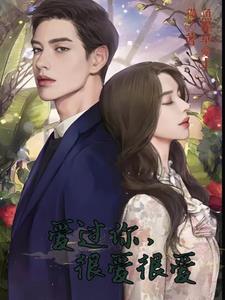第65章 郝县长的震撼
!有俺们原上的,还有好几百的外乡灾民!”
“灾民?愿意出力帮白鹿原修水渠?”
老丈撇撇嘴:“白家大少爷说了,帮着挖渠就能吃饱饭,不帮就喝稀的,现在这大灾之年,能混口饭吃多不容易啊,俺们村好多后生都去了,要不是俺这把老骨头实在不中用,俺也想去出把力气!”
郝伟成心里又是一动。这已不是他路上第一次听到“白家大少爷”这个名字了。从离开县城起,凡是谈到白鹿原,谈到赈灾,必然提到此人。
“走,去白鹿村!”郝伟成不再犹豫,挥手下令。目标明确——他要亲眼看看修水渠的“热闹场面”,更要见见那位神通广大的“白家大少爷”。
……
一路走了快一个多小时,终于靠近了白鹿村。
绕过一道布满尘土的黄土梁子,巨大的喧嚣声浪伴随着热风扑面而来。郝伟成猛地驻足,饶是有所准备,眼前的景象仍让他心头剧震。
一条宽阔的、初具雏形的人工水渠,如同一条巨大而丑陋的伤疤,硬生生撕裂了白鹿原干涸灰黄的地面,向着远处延伸。河道上下,人头攒动,密密麻麻,蚁群般的人影在灼热的空气中浮动、攒动。
水渠施工的地方,是光着膀子、精赤上身的汉子们。他们大多皮肤黝黑,突出的肋骨清晰可见,汗水混合着泥土,在身上冲刷出无数道泥浆溪流。他们挥舞着原始的镐头、铁锹,奋力刨挖着坚硬的土石。
每一次镐头落下,都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嘿嗬”,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的号子,粗粝、沉闷,却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韧劲。
飞扬的尘土如同黄色的烟瘴,笼罩着这段河道,模糊了他们的面孔,只剩下一个个奋力挥动的身影轮廓。
阳光直射,汗水滴落在地表瞬间蒸发。
河道上方两侧,则分布着大量的挑土工。
扁担挑着沉重的装满泥土的藤筐、箩筐,咬着牙,脖颈上青筋暴起,脚步沉重却坚定地走向远处的弃土堆。
灾民的队伍和本地的村民队伍混杂在一起,同样的灰头土脸,同样的汗水淋漓,但从他们的眼神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白鹿原的村民,哪些是灾民。
灾民们目光紧盯着前方分发食物的凉棚,那是支撑他们机械重复的动力,而村民们眼里盯着的是修好的水渠,那是他们往后的饭碗,孩子上学的花销……
在河道的几个关键节点,穿着略显整齐的粗布短褂、头戴草帽或裹着毛巾的青壮年显得格外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推背镇守使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河山清)的经典小说:《推背镇守使》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052266字10-01
- 82年:学猎养狗训雕的赶山生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樱十九)的经典小说:《82年:学猎养狗训雕的赶山生活》最新...
- 1104350字10-01
- 爱过你,很爱很爱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鱼腥草爱上猫)的经典小说:《爱过你,很爱很爱》最新章节全文...
- 572688字10-13
- 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茫的砂砾)的经典小说:《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1244383字06-14
- 重生七零:团宠拿捏了首长大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月见不再见)的经典小说:《重生七零:团宠拿捏了首长大人!...
- 558843字06-10
- 渣男忘恩负义?重来让你断子绝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素霏霏)的经典小说:《渣男忘恩负义?重来让你断子绝孙》最...
- 1271484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