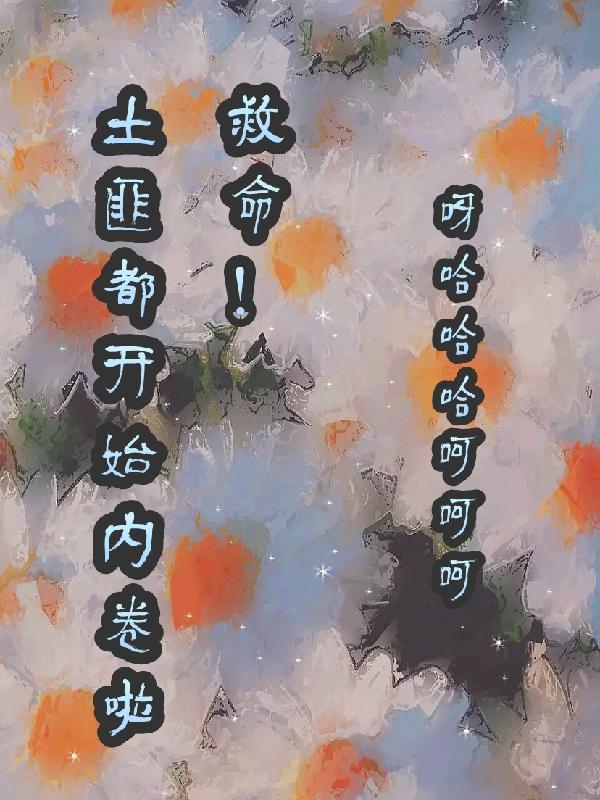袁隆平等走访转基因实验田
了杂交稻的突破。”
老人家从裤兜摸出个布包,里面是他珍藏的野生稻标本,稻芒扎手却泛着野性的光,“有人说杂交稻是‘自然的’,转基因就不是?错了!人类驯化作物的每一步,都是在和基因‘打交道’。你看这野生稻,亩产才几十斤,现在咱们的抗虫稻能收上千斤,靠的就是把好基因‘搬’过来——这不是违背自然,是自然教给咱们的本事。”
三、风里的诗行
暮色漫过田垄时,助理小陈博士抱来一摞实验报告,纸页间夹着各地农民寄来的感谢信。河北棉农寄来的锦旗上,“虫口夺粮”四个大字被晒得褪色;湖北稻农编的草帽里,藏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里的人穿着褪色的衬衫,站在齐腰的稻浪里比着“丰收”的手势。
袁隆平忽然从兜里摸出粒花生,掰成两半分给众人:“1959年饿肚子,我在田里捡稻穗,捡着捡着就想——要是能让稻穗比花生还大,该多好。”他把花生壳埋进泥里,“现在你们做到了,用基因编辑让稻穗结满籽,这不是‘逆天’,是‘顺天’——顺着老百姓的天,顺着土地的天。人类从改良种子那天起,就在做‘转基因’的事。远的不说,就说咱们吃的玉米,几百年前还是墨西哥的野草,靠的就是一代代‘转’基因才变成今天的模样。”
何祚庥望着远处基因楼的灯光,忽然背诵起《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两千年前屈原问天道,今天我们用基因剪刀回答——自然不是供人叩拜的神龛,是等着被读懂的天书。搞转基因,不是要当自然的主子,是要当自然的学生,把它藏在DNA里的学问,变成老百姓锅里的米、身上的衣。就像候鸟迁徙、松鼠储粮,人类用科学优化作物,本质上和蜜蜂筑巢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他的眼镜片映着稻浪,镜片后的目光像极了张启在实验室看显微镜时的专注。
夜风掀起张启的蓝布围裙,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衫,第二颗纽扣永远松着,露出锁骨下方的烫伤疤痕——那是1986年第一次转基因实验时,烧杯炸裂留下的。
他望向天际,银河正在云层后铺展开来,每颗星都像一粒待播的种子,而他脚下的泥土,正是孕育星辰的子宫。
“搞农业的人,”他忽然开口,声音混着稻叶的沙沙声,“要把自己种进地里。你看这抗虫稻,根扎得深,秆子才直,穗子才沉——就像咱们搞科研,身子扑得下泥土,心才能接上星空。转基因从来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是人类向自然借的一把镰刀,割开蒙在真相上的杂草,让阳光照进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欲!他野得犯规
- 欲!他野得犯规章节目录,提供欲!他野得犯规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856913字07-22
- 赶海:我靠赶海养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只想当一名肥宅)的经典小说:《赶海:我靠赶海养娃》最新...
- 2274968字07-19
- 隔壁大佬总在觊觎我
- 607216字07-19
- 救命!土匪都开始内卷啦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呀哈哈哈呵呵呵)的经典小说:《救命!土匪都开始内卷啦》最...
- 691233字07-20
- 我在美漫做惊奇蜘蛛侠
- 985474字07-22
- 选秀逆袭从祭天剧本成为C位出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黑白瓷)的经典小说:《选秀逆袭从祭天剧本成为C位出道》最新...
- 747375字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