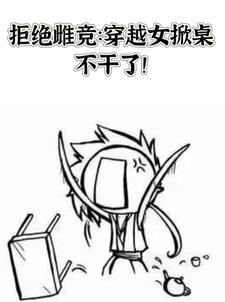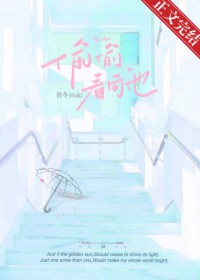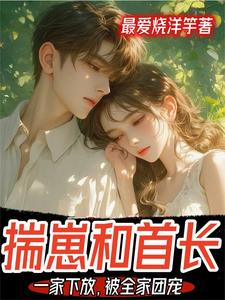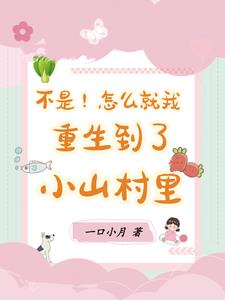袁隆平等走访转基因实验田
华中农业大学的试验田在大暑节气浸在蜜色的阳光里。张启蹲在田埂上,指尖抚过抗虫稻的叶片,叶脉间的Bt蛋白晶体折射着碎光,像极了童年时见过的萤火虫——那时他跟着父亲在夏夜巡田,裤兜里装着母亲用旧报纸折的萤火虫灯笼。
远处的蝉鸣忽然密集起来,他抬头望去,一辆老式中巴车正碾过碎石路,车窗外闪过的白衬衫领口,让他想起实验室里永远晾着的、洗得发灰的工作服。
一、穗尖上的年轮
袁隆平院士的布鞋最先踏上田埂,鞋面缝着的橡胶补丁在阳光下泛着油光。
“启老弟,”老人的湖南话混着稻花香,“你这稻秆硬得能当扁担使,当年我在安江农校啃窝头搞杂交,要是有这抗虫本事,早把‘三系法’捧上天了!”他腰间的牛皮皮带还是1964年那块,扣眼磨得发薄,却依然勒着笔挺的腰板。这位在稻田里写就“禾下乘凉梦”的老者,此刻正用拐杖尖拨弄着转基因稻的根系:“看这须根,比传统稻密三成,扎得深啊——人跟稻子一个理,根基稳当,说话才响。”
何祚庥院士下车时撞响了车门上的防蚊帘,这位理论物理出身的老者竟穿着条卡其布工装裤,裤兜鼓鼓囊囊装着光谱仪和笔记本。
“我给大伙带了件礼物,”他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刚从实验室带来的转基因棉花标本,棉纤维在阳光下泛着珍珠光泽,“当年搞氢弹原理,有人说‘这是要烧穿大气层’,如今咱们搞基因编辑,道理一样——都是解开自然方程式的笔。”他忽然指向稻田里的荧光标记,“你们看这抗虫基因的表达曲线,像不像我当年推导的粒子对撞轨迹?自然规律本就相通,人类不过是学会了用不同的笔书写。就像远古人驯化小麦,不也是把野生麦的基因‘转’进农田里?咱们只是把这过程从千年缩短到十年。”
陈君石院士的保温杯腾着热气,杯身上“食品安全卫士”的字样被磨得模糊。
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他的白大褂口袋永远装着消毒湿巾,此刻却任由稻叶上的露珠沾湿袖口:“我研究了一辈子膳食风险,最清楚‘恐惧’才是最大的毒素。就像这碗米饭,”他指了指张启递来的转基因稻米,米粒在粗陶碗里泛着青玉光,“要经得起质谱仪的推敲,也要经得起老百姓的舌尖。老祖宗早就知道‘民以食为天’,咱们搞转基因,不是要改天换地,是要让这天,更蓝,这地,更肥,这饭,更香。你看这稻种抗虫又耐旱,不正是老辈人说的‘顺应天时’?”
二、泥土里的星河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美综:家族教父,和平大使什么鬼
- 734644字07-19
- 女帝谢樱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栗子)的经典小说:《女帝谢樱传》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099587字07-21
- 偷偷看向他
- 偷偷看向他章节目录,提供偷偷看向他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706552字07-21
- 快穿之女人何苦
- 1081543字07-21
- 揣崽和首长一家下放,被全家团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最爱烧洋竽)的经典小说:《揣崽和首长一家下放,被全家团宠》...
- 578603字07-20
- 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口小月)的经典小说:《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1134522字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