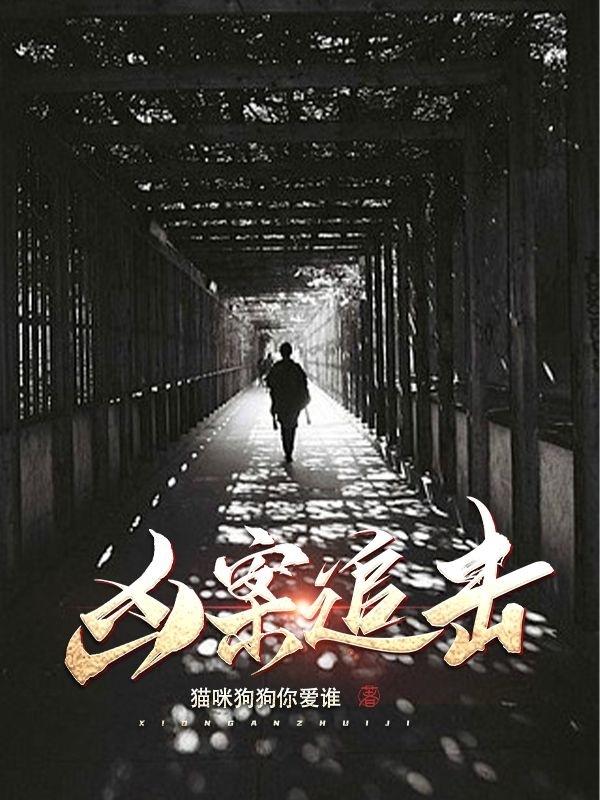第 136 章 番外
。
十五岁的蔺泊舟,从罹患眼疾后在许多人间温情上,变成了极度别扭和僵硬的人,父亲和母亲为他的双目可惜,他于是越发恨这双眼睛,其他人避之如蛇蝎,连提都不敢提,没有人敢触及他这处伤痕。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美色固然有美色的好处。既然母妃要他身边有人,那眼前这个,他愿意要。
“疼吗?”
怀裏的身躯温热柔软。
孟欢声音慌张:“你才十五岁!我不行,不可以,不要!”
“你太小了我不行,呜呜呜我不行,”虽然大宗婚龄早,但孟欢不能接受,他摇头,“我是来安慰你的,不是,不是想和你那个,反正绝对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呜呜呜你别说荤话了,听着好像犯罪。”孟欢拼命摇头,“不行,不行,不是现在,现在不行,不能圆房。”
他对孟欢的说法不甘,攥紧他的手腕,重重握着。
孟欢:“是,但不是现在。”
声音执着,宛如当头棒喝。
孟欢喉头滚动,明明很简单的话,可忽然感觉说不出来。
孟欢手腕挣扎的力道缓和:“蔺泊舟。”
孟欢勾着手指,拽掉了那一缕白纱,他往上,微凉的唇贴近吻他纤薄的眼皮。蔺泊舟轻轻颤抖了一下,双手抓紧孟欢的肩头,力气先是极重,似乎要陷入骨髓中,随着亲吻才逐渐松缓下来。
他初知人事,第一次动情。
“记住我说的话,你一直熠熠生辉。在遇到我之前的这十几年,照顾好自己。”
天漆黑,屋子裏只有一盏很暗的烛火,摇摇欲坠。
回去了。
孟欢坐起身,亲了亲他的脸:“好好长大,好开心啊。”
孟欢嘻嘻一笑:“我叫孟欢,孟夫子的孟,欢愉的欢。”
孟欢慢慢变淡,直到变成了一缕空中的意识,看见蔺泊舟撑身坐起,床榻中,他手指轻轻摸索身侧,摸到一片空白时,他长睫微微颤了一下,掌心反复确认。
蔺泊舟垂头坐着,修长的手指浸在金盆裏,静了好一会儿,冷不丁问:“昨夜,母妃送来陪侍的下人呢?”
少年怔了下,说:“是吗。”
突然,他膝盖不慎撞到身旁的梨花木椅子。
他只是梦境中的一缕意识,发不出任何声音。
——相隔无数。
相关小说
- 劫天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浮梦流年)的经典小说:《劫天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24301574字07-29
- 凶案追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猫咪狗狗你爱谁)的经典小说:《凶案追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177476字07-30
- 怪谈游戏设计师
- 医生,我做的游戏好像变成了现实。这不挺好吗?现在人们工作压力那么大,你却能够摆...
- 1926624字07-30
- 鬼眼话事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用挚爱守护你)的经典小说:《鬼眼话事人》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322000字07-30
- 神豪从天刀开始
- 突然回到几年前,还获得了个游戏富婆系统。有钱了,也失去了点东西。混在游戏圈当个...
- 1775129字12-26
- 无尽灰夜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柯辟邪)的经典小说:《无尽灰夜》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2014066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