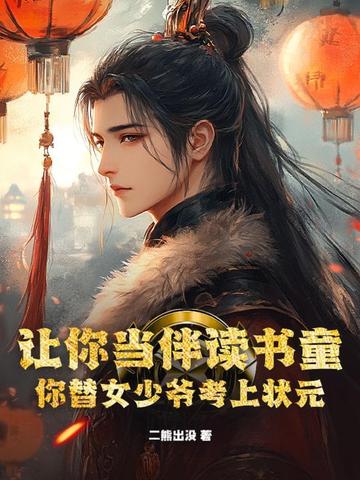第438章 奇吉林之战1
在明国遥远的西方,横亘在亚欧非三大洲交汇之处的庞然大物,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由奥斯曼一世于公元1299年建立的帝国,至1675年,已傲然屹立了近四百年之久,苏丹的宝座已传承了十数代。
奥斯曼帝国扼守着东西方贸易的咽喉,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令欧洲贵族趋之若鹜的珍宝,必须经过奥斯曼人的手才能流入西方。
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匹在东方价值十两银子的上等丝绸,经奥斯曼商人之手辗转至威尼斯或巴黎,其价竟可高达千两!欧洲人对此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奥斯曼的铁骑与新月弯刀太过强大,数百年间无数次“圣战”的失败早已证明,基督世界的联军难以撼动其根基。正是这令人窒息的贸易壁垒与军事压力,迫使欧洲人扬帆远航,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从而阴差阳错地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
如今,时间流转到1675年的春天。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巍峨耸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深处的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如铁。
巨大的波斯地毯上,帝国真正的掌舵者,大维齐尔(Grand Vizier)**科普鲁律·法佐·艾哈迈德帕夏**(K?prülü Faz?l Ahmed Pasha),正与帝国最核心的军事统帅们围在一张描绘着黑海北岸广袤土地的巨幅地图前。烛光映照着他深邃而略显疲惫的面容,这位刚刚征服了克里特岛、令威尼斯屈膝的传奇宰相,此刻眉头紧锁,目光死死钉在地图上那个被第聂伯河蜿蜒环绕的要塞——**奇吉林**(Chyhyryn)。
“诸位帕夏、贝伊,” 法佐·艾哈迈德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穿透力,手指精准地点在奇吉林的位置,“形势危急如燎原之火!去年,真主庇佑,我们英勇的将士如雄狮般撕开了波兰人的防线,将波多利亚(Podolia)收入囊中,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ianets-Podilskyi)的十字架已被新月取代!我们扶持的右岸盖特曼,**彼得罗·多罗申科**(Petro Doroshenko),如雄鹰般翱翔在第聂伯河右岸,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支点。”
他顿了顿,手指重重敲击地图上奇吉林的标记,语气转为严峻:“然而,沙皇那头贪婪的北方巨熊,绝不会坐视我们整合乌克兰!那个背叛了多罗申科、投靠莫斯科的左岸盖特曼,**伊万·萨莫伊洛维奇**(Ivan Samoilovych),在沙俄的操纵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道侣飞升跑路,我薅哭全宗女修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醉酒大萝卜)的经典小说:《道侣飞升跑路,我薅哭全宗女修》最...
- 1509004字10-01
- 让你当伴读书童,你替女少爷考上状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二熊出没)的经典小说:《让你当伴读书童,你替女少爷考上状元...
- 405027字10-01
- 穿成狐妖后,我成神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枝心月)的经典小说:《穿成狐妖后,我成神了》最新章节全文...
- 534798字10-01
- 戏假成真:演癮君子这么像?查他
- 389803字07-30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956967字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