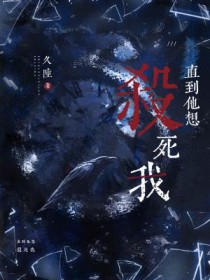第114章
十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什么不能习惯的?可是,昨晚的梦里,我变得痛苦。痛苦得无法忍受,一直在尖叫,最终愤怒又暴躁的打碎了面前的箱子,说:我不!”
“箱子碎了,我醒了,眼角都还流着眼泪。”
“不知道怎么的,我在梦里砸碎的箱子,好像是电影里的那个箱子,只是里面紧锁的不再是电影里一个个虚构的受害者名字,而是曾经无人问津的我自己。而我像林荫一样,明明不想活了,却固执的和死亡搏命,只为了打开这个箱子。”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电影为什么称呼它为无法打开的箱子。”
“原来,箱子里困住的是我。被杀死的也是我。”
影评人的梦境感慨,比第一天的收钱办事更叫人共情。
他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在读的学生,还是工作已久的社会人,都曾经被父母寄予厚望。
那些厚望扭曲了他们的自我,抹杀了他们的个性,让他们混沌的走入社会,毫无准备的去面对残酷现实,差点迷失在人生的路上。
听话、懂事,变成了他们受害的主旋律。
引得一个又一个受害者聚在这篇梦境分享之下,发出一句又一句共鸣。
“我以为纱纱不会有这种烦恼,因为你活成了我羡慕的模样,想不到我们一模一样。”
“比起昨天推荐说《箱子》的故事和演技,我更喜欢你今天说的梦境。”
“买票了,我也要去看看箱子里困住的我。”
比起那些表面好评,发自内心的感慨,带动了更多人准备去电影院一探究竟。
不少人觉得太夸张了吧,为了推荐一部电影,把自己童年阴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6页

![我才不是人外龙傲天的老婆[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6/66740/66740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