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根底干净,这会属实是无妄之灾。
这份自觉冤屈乃是搅动白水的一匙糖底,不是招待客人用的,却叫后一个用碗误会了甜味,自觉脸上得了光。于是连心也安稳下来,以为自己仍是座上宾,不怕主人家逐客,还能冷眼看着门外人嚷嚷。
真切把糖块化在白水里,一小盏也作了肥水,慢慢挪动着影和光。许忆湘瞧着一小碗糖水发怔,手颤抖着,恐惧与茫然一应被填补。
她就这样,她和大嫂就这样把证据交付......
那之后,张家要落个什么下场呢?
许忆湘不自觉打个寒噤,好像有谁憋着一口冷气在她耳后打个喷嚏。但她脸上又带着十足的庆幸——喷嚏打出来,之后便不会叫鼻子发痒,时时惦记。
这样的喷嚏打出来,先是庆幸,继而是为难,再稍后时刻,搅动碗里的甜水,心里却生出无限期待。
她做张家二房奶奶已经太久,顺应了怯懦依从的假面,成全了丈夫骨子里的难堪。一二三四五年,年年相同,再往后的日子也没什么分别。
他们会死,他们都会死。手打的巴掌和嘴打的巴掌样样记得,他们的报应是她引过来,她是报了自己的仇怨。
一颗眼泪被粘稠的糖水包裹,许忆湘俯下身,肩膀一耸一耸,像是哭喊,离得近了,却又听到细微的笑。
一件衣裳披上,把后颈、臂膀都遮盖。轻柔的动作好像唯恐搅扰她,许忆湘知道是谁,她的笑声低垂,捧着的糖水变得稀薄起来。
拢着她的人声音也轻,许忆湘的笑溢出喉咙——想着这个人比她小不知道多少个春秋。
帕子沾在眼角,许忆湘缓了半刻,反跟黛玉道:“我听说府中有紧急事,索性东西也交上去,走不脱的总也走不脱,夫人不必太顾念我。”
相关小说
- 快穿,从太阴星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只摩羯)的经典小说:《快穿,从太阴星开始》最新章节全文阅...
- 1181096字09-28
- 万妖圣祖
- 半妖少年,得妖族圣典,化天狼吞月养女鬼为仆,变朱雀焚天煮海,立白虎大杀四方,修神龙...
- 26863601字07-06
- [文野同人] 太宰君不想长大
- [文野同人] 太宰君不想长大章节目录,提供[文野同人] 太宰君不想长大的最新更新章节...
- 1497033字07-24
- [综漫] 啊?我当老师
- [综漫] 啊?我当老师章节目录,提供[综漫] 啊?我当老师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77903字07-27
- (综漫同人)海露谷物语
- (综漫同人)海露谷物语章节目录,提供(综漫同人)海露谷物语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3519089字07-27
- 无名江湖录之九阴日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作家FuvlBt)的经典小说:《无名江湖录之九阴日记》最新章节...
- 1576693字1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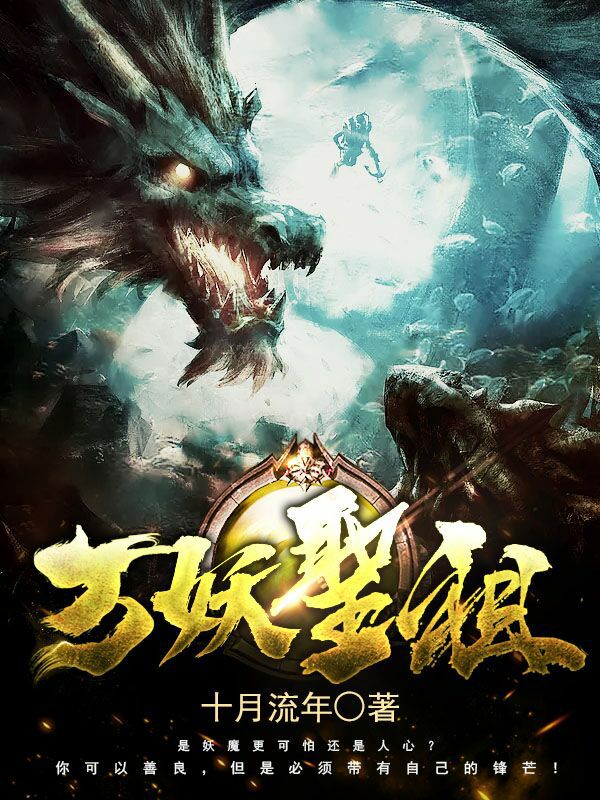
![[文野同人] 太宰君不想长大](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4/64931/64931s.jpg)
![[综漫] 啊?我当老师](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6/66071/66071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