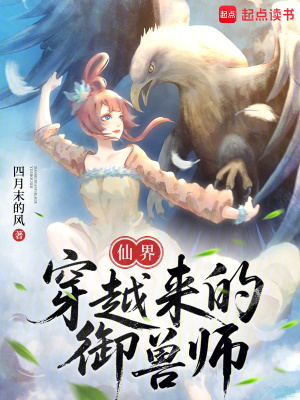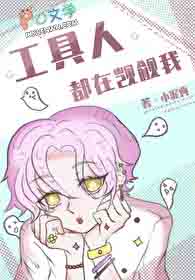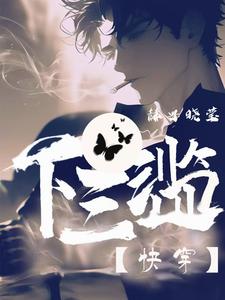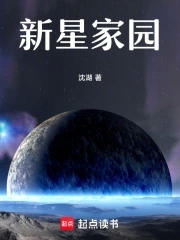第248章 皇帝的朱批:朕知道了(其实啥也不知道)
缚对皇帝的朱批早有预料。他让人把新稻种分发给农户,不管朝堂怎么吵,先种下去再说。陈老兵分到稻种时,捧着稻种哭了 —— 他老家就在盐碱地,一辈子没见过地里长粮食,现在,居然有稻种能在那里生长。
“林大人,这稻种要是能长起来,俺们老家的人,就再也不用挨饿了。” 陈老兵抹着眼泪说。
林缚拍了拍他的肩膀:“肯定能长起来。皇上批了‘朕知道了’,就是让咱们放心种。”
其实林缚心里清楚,皇帝哪是 “知道了”,他是 “啥也不知道”—— 不知道新稻种的原理,不知道军屯的难处,甚至不知道朝堂上的争吵,哪些是为了国事,哪些是为了私怨。但皇帝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 “不知道” 的时候,最好别瞎指挥,让懂的人去干。
这种 “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时候比 “啥都想管” 强。
秋收时,京郊试种的新稻果然长出来了,虽然产量不高,但在盐碱地里,已经是奇迹。工部的人把稻穗送到宫里,崇祯拿着稻穗,看了又看,突然对王承恩说:“你看,这稻穗上的颗粒,比奏折上的字实在多了。”
王承恩点点头:“是啊,皇上,这才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崇祯没说话,拿起朱笔,在军屯的奏报上,写下了四个字:甚好,推广。
这是这么久以来,皇帝第一次没写 “朕知道了”。
消息传到军屯,林缚正在给稻种脱粒。赵虎拿着抄来的朱批,高兴地喊:“大人!皇上让推广新稻种了!”
林缚笑了,拿起一粒稻谷:“你看,不管朝堂怎么吵,不管皇帝知道不知道,这稻谷该长还是会长。咱们要做的,就是让它长得更好。”
远处的田埂上,陈老兵正在教孩子们辨认稻种,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孩子们的笑声,稻穗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水车转动的吱呀声,混在一起,像一首踏实的歌。
这首歌里,没有朝堂的争吵,没有皇帝的朱批,只有土地和汗水,只有生长和希望。
崇祯皇帝站在皇宫的角楼上,望着远处的田野,手里还攥着那支新稻穗。秋风拂过,稻穗轻轻晃动,像在告诉他:这世上的事,其实很简单,把该种的种下,把该浇的水浇上,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
至于那些争吵和朱批,就像田埂上的杂草,不用太在意,拔了就是。
皇帝轻轻叹了口气,转身回宫。明天,朝堂上还会有新的争吵,还会有新的奏折,但他知道,有些东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求生:魔法灾变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水沧澜)的经典小说:《求生:魔法灾变世界》最新章节全文...
- 1323949字11-23
- 仙界穿越来的御兽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四月末的风)的经典小说:《仙界穿越来的御兽师》最新章节全...
- 287048字07-27
- 工具人都在觊觎我
- 工具人都在觊觎我章节目录,提供工具人都在觊觎我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62282字07-23
- 【快穿】下三滥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赫鲁晓莹)的经典小说:《【快穿】下三滥》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829588字07-24
- 新星家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沈湖)的经典小说:《新星家园》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1044367字12-15
- 它贴着一张便利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红枫霜月)的经典小说:《它贴着一张便利贴》最新章节全文阅...
- 2635094字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