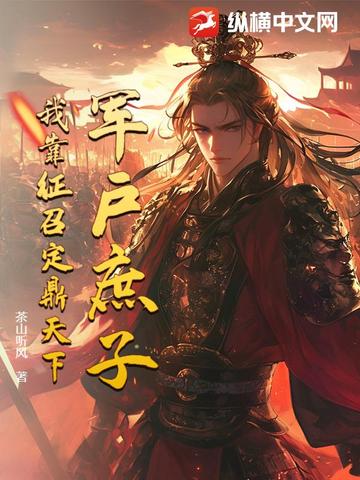第211章 拓土筑基:钢铁化工的雏形与两洋防线
钢铁厂的第一炉“硫磺钢”出炉时,李匠头特意请部落首领来观礼。钢锭泛着暗蓝色,用锤子砸,只出白印,不碎裂。“这钢能造更好的铁轨、更利的炮管。”他说着,让人用这钢轧出第一根新铁轨,比旧铁轨粗了半寸,铺在西境工业区的轨道上,蒸汽机车跑上去,稳得几乎不晃。
葡萄牙人的“试探”来了。他们派了艘“商船”,装着香料、丝绸,想停靠连湾港,说“想换些北美特产”。吴兑按规矩验了货,只允许他们在指定区域交易,派印第安营士兵“陪同”(实则监视),绝不让他们靠近码头仓库(里面堆着硫磺矿样品)。交易时,葡萄牙商人旁敲侧击问“沙湖以西有啥”,吴兑笑着说“只有沙子和野鹿”。
西境工业区的“共益仓”比铜矿的更丰盛。除了分利,还多了“技术股”——部落人若发现新的矿脉,奖励玻璃珠一串、铁钱十文;移民工匠若改良工具,奖励硫磺皂十块、稻米五斗。一个雪松部落的老猎人,在巡逻时发现了露天煤矿(比木炭更耐烧),吴兑当场奖了他一头牛,说“这比十串玻璃珠还实在”。
“铜铁学堂”开了“化工课”。化工工匠用硫磺、硝石、木炭做简单的化学反应(不点火,只看颜色变化),教孩子们认“能让铁变软的水”(硫酸)、“能让肥皂发泡的石”(硫磺)。一个移民孩子问:“能做让炮更厉害的药吗?”陈大人摸摸他的头:“先学好认矿石,以后教你做。”
这日,林远在西境堡垒召开“拓殖会议”。黑板上画着扩大后的北美地图,沙湖以西用红笔标着“工业区”,旁边写着“铁、硫、煤”;山口处标着“西境堡垒”,旁注“防葡、西”。吴兑说:“按现在的进度,明年春天,西境能产钢锭百吨、硫酸五十桶,够供连湾港和北门锁钥的用度。”
赵武指着地图上的葡萄牙据点:“已派盐粒带十名印第安营士兵,混在秘鲁部落的商队里,去摸清他们的船数和炮数。”林远点头,让人把新炼的硫磺钢炮图纸发给王工匠,“再铸两门,一门送西境堡垒,一门送雾湾,让他们知道咱的铁不是好惹的”。
夕阳把西境工业区的烟囱染成金色,高炉的火光与晚霞交映,铁轨上的蒸汽机车拖着钢锭,像条游动的铁龙。部落人在铁矿旁唱着新编的歌谣:“黑石头(铁矿),黄石头(硫磺矿),炼出铁来盖新房,打跑坏人保家乡。”
林远站在堡垒的炮座上,望着远处正在铺设的铁轨(一直通到沙湖),心里清楚,这片扩大的土地上,钢铁是骨,化工是血,人心是魂。有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本来只想带崽,结果全师门都跟我混
- 284359字07-23
- 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茶山听风)的经典小说:《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最新章...
- 611379字07-26
- 血炼妖帝
- 2663288字07-25
- 霸天武魂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千里牧尘)的经典小说:《霸天武魂》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1329324字07-26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