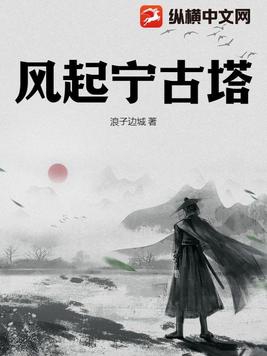第20章 纸书横空出世,天下风动
典籍自董卓迁都后损毁过半,天子若准了,我们派工匠去修阁,实则是..."他指尖点在"修缮"二字上,"抄录全本,藏于临淄。"
糜竺猛地抬头,眼底闪过精光——东观是汉室藏书最丰之处,若能将那些孤本抄成纸书,莫说天下士人,连各郡太守都得派人来临淄求书。
"可这会不会让天子生疑?"刘备捏着奏疏,眉峰微蹙,"孤虽为皇叔,到底是外臣。"
"天子如今在长安,被李傕郭汜架空,最缺的就是'仁德'的名声。"陈子元望着窗外招贤馆飘起的书幡,"明公献书,是替天子行教化;修阁,是替汉室存文脉。
他若不允,反显得薄了圣德。"
刘备沉默片刻,突然笑了:"子元这是要让临淄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根。"他将奏疏递给糜竺,"速着人备车马,挑最上等的纸书,明日就送长安。"
同一时刻,千里外的徐州下邳。
糜竺派去的家仆正站在州牧府门前,将一卷《匠户考绩例》呈给陶谦的主簿。
而在城中心的布告栏前,新贴的告示被晨风吹得哗哗响:"临淄将建'稷下书院',广纳天下大儒,凡有着述者,书院免费刊印纸书,传于九州。"
第一个看到告示的是个穿葛衣的老秀才,他扶了扶破眼镜,手指抖着念完最后一句,突然转身朝客栈跑——他昨夜刚写好的《春秋注》还压在包袱底,此刻恨不能立刻捆了铺盖奔临淄。
三日后,临淄城的城门便热闹起来:穿深衣的经师提着书箱,背布囊的学子扶着老父,连吴郡的隐士都坐着牛车来了。
招贤馆的仆役搬来长凳,在门前支起茶棚,远远就能听见南来北往的口音:"听说书院有纸坊,写本书能印百册?不止,我同乡说,连《齐民要术》都要刊纸本,农人们不用凑钱抄竹简了!"
而在临淄的税曹,陈宫捏着新报的账册直笑。
纸坊的税银比上月翻了三倍,更妙的是——卖纸的商队带来了蜀锦、吴盐,买纸的士人留下了笔墨、碑帖,连青州的粮价都因商路畅通降了两成。
他抬头望向窗外,招贤馆的读书声与造纸坊的捣浆声混在一起,倒比当年在洛阳听的编钟更入耳。
可这一片热闹,终是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
"报——"王越撞开议事厅的门,腰间的铁剑撞在门框上,发出闷响。
他铠甲上还沾着血点,额角的汗顺着下颌滴在青石板上,"管亥率十万黄巾,围了北海都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镜
- 66958字07-23
- 帝无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南华无忧)的经典小说:《帝无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014148字07-15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开天辟地见苍凉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佚81194)的经典小说:《开天辟地见苍凉》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4582058字07-15
- 风起宁古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浪子边城)的经典小说:《风起宁古塔》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680191字07-24
- 赠礼返还,谁规定不能当舔狗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渊梦)的经典小说:《赠礼返还,谁规定不能当舔狗了!》最新...
- 593818字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