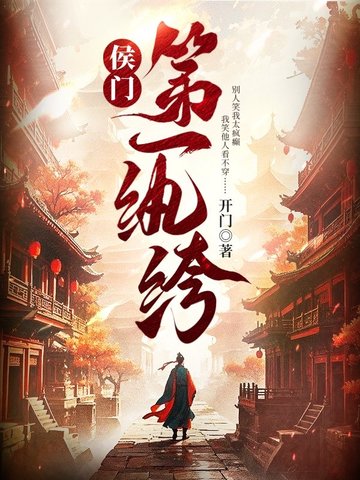第17章 招贤纳士,风云汇聚
在商路图上的“泰山”二字,“可托泰山郡的孙掌柜带话,就说‘刘使君的仁义,能保糜家三代富贵’。”
糜竺的眼睛亮起来,他猛地站起来,锦靴磕在案脚上发出闷响:“在下这就修书!今日午后便让长子押第一车粮草出发!”他转身要走,又顿住,从怀中摸出个檀木匣,“这是在下私藏的二十张耕牛契,虽不多,但春耕时总能解些农户的急。”
刘备接过木匣,指腹抚过契上的红印,声音发哽:“子仲……”
“主公莫要谢我。”糜竺弯腰行了个大礼,起身时眼眶发红,“是在下该谢主公,给了糜家做人事的机会。”他倒退两步,转身时衣摆带起一阵风,吹得案上的《招匠令》哗哗作响。
那声响像是一根针,挑断了时间的线。
荆州,新野城外的竹庐里,郭嘉正用竹箸拨弄冷掉的粥。
窗外传来差役的吆喝:“刘使君的《招贤令》贴到城南了!说不论出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领米三斗!”他手一抖,竹箸“啪”地断成两截。
记忆突然涌上来——三个月前在洛阳酒肆,他遇见个穿青衫的年轻人,对方举着酒碗说:“郭兄可知,真正的大势不是兵马,是人心?曹操有虎豹骑,袁绍有河北粮,可他们缺的,是愿意替他们把政令传到每寸土地的人。”
郭嘉盯着断成两截的竹箸,突然笑出声。
他扯下墙上的《六韬》卷,塞进青布包袱,又把案头的算筹全倒进包袱角。
出门时踢到门槛,他也不扶,只是大步往马厩走,边走边喊:“阿福!备马!去临淄!”
长江上,一艘乌篷船正逆水而行。
船头立着个赤膊大汉,古铜色的脊背被太阳晒得发亮,他拍着船舷吼:“艄公!再加把劲!老子要赶在曹操的兵到临淄前,把这对板斧献给刘使君!”
长沙城外的铁匠铺里,七十岁的张师傅蹲在炉前,用铁钳夹起烧红的犁头。
火星溅在他手背的老茧上,他却笑得眯起眼:“娃子们,把我那套铸剑模子收进木箱。临淄的招匠馆说能给匠户立谱,老子这把老骨头,还想再铸十把好犁!”
临淄城头,陈子元扶着城砖远眺。
晨雾散了,官道上像爬着一条灰黑色的长虫——那是投奔招贤馆的人群,有背着书箱的少年,有挑着工具箱的匠人,甚至还有几个裹着粗布头巾的农妇,怀里揣着自己编的竹器。
可他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镜
- 66958字07-23
- 侯门第一纨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开门)的经典小说:《侯门第一纨绔》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656984字07-05
- 帝无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南华无忧)的经典小说:《帝无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014148字07-15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修仙家族之化灵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啸天灵狼)的经典小说:《修仙家族之化灵碗》最新章节全文阅...
- 4067736字07-22
- 开天辟地见苍凉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佚81194)的经典小说:《开天辟地见苍凉》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4582058字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