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女子禁考,别想科举逆袭
家政为主。
清政府在1907年才首次尝试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目的是培养女子教师,而不是开放仕途。1905年科举废除前,女性依然完全没有参加科举的渠道。民国之后虽取消科举制度,女性才逐渐获得教育与考试的机会,但那已经是20世纪的事情。
换句话说,在古代,无论是否设有女学堂,女子与“应试取士”的路径都没有交集。不存在“偷偷进女学,再冲刺科举”的可能。
即便某些作品绕开了考试资格限制,安排女子“匿名应试”“天降奇才”,但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员,而女子无仕途,无从实现“逆袭”。
在古代社会结构中,男子考中举人、进士,可直接进入官僚系统,从县令、主簿、知府一直升至宰相。而女子,即使写出八股文,拿到“状元”,也无处安放。她既无法入朝为官,也不能参与治理,顶多成为“私塾女师”、“家中幕僚”之类边缘身份。
《明史》中记载的“文士女子”往往只能靠着书立传或成为文人之妻,在私领域发挥才学,远远无法像男士一样“朝堂有位”。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女子科举逆袭”根本无从实现。
“才女”不等于“官员”,社会评价体系不同。历史上确实有众多才女,但她们与官员体系是完全脱钩的。比如李清照、班昭、蔡文姬,她们的文学、史学、书法成就斐然,但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内修其德”,而非“外任其职”。
清代女性作家纪昀的夫人“刘氏”,据称能背诵《春秋》,评论文章不输丈夫,但她的地位仍然局限于家庭。“妇德”、“贞节”、“女训”始终是社会对才女的道德底线,若敢越雷池一步,反而会被视作“不守妇道”。
简而言之,才华可以有,但必须藏于闺阁,不得外显;作品可以传,但最好署夫姓。这种根深蒂固的礼教伦理,使女子“靠文采搏仕途”的幻想彻底落空。
古代科举竞争极其激烈。据《清会典》记载,清代会试时每次参考者约六千人,录取者不过三百,录取率仅5%;乡试中举比例更低,仅2%左右。哪怕是寒窗十年、父祖三代耕读积累的男性,也多半落榜收场。
在这样严苛的考试体系中,女性即使有机会入场,所面临的竞争和资源劣势更难逾越。连男性都“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女性根本没资格上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此外,考试费用高昂,需置办应试服饰、书籍、长年备考支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带着仓库到大明
- 带着仓库到大明章节目录,提供带着仓库到大明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8289760字07-24
- 南华曲
- 南华曲章节目录,提供南华曲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306129字07-24
- 路人甲选择干翻全星际
- 路人甲选择干翻全星际章节目录,提供路人甲选择干翻全星际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851903字07-24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秦汉纵横家
- 1661922字07-04
- [快穿]直男男二也要被觊觎吗
- [快穿]直男男二也要被觊觎吗章节目录,提供[快穿]直男男二也要被觊觎吗的最新更新章...
- 833333字0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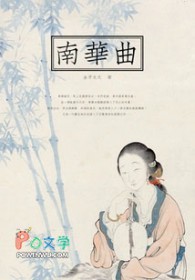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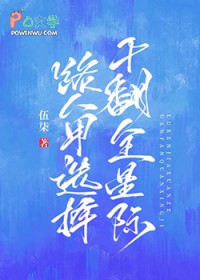


![[快穿]直男男二也要被觊觎吗](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3/63507/63507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