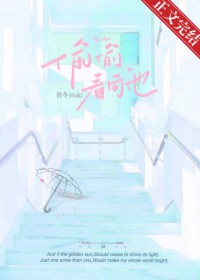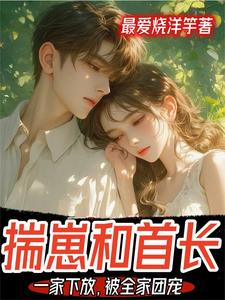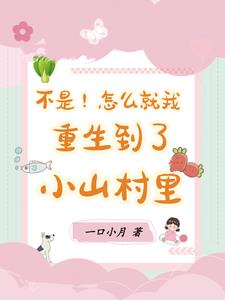第131章
塔》里洛丽塔那早早死去的母亲、《漫长的季节》里沈墨那没有话语权的伯母……
我想,这也是冥冥之中我没有把《夜以继日》里严冬的母亲杜俊芳作为“声讨对象”的原因。
因为无论这些母亲强大还是弱小,她们某种程度也都是“受害者”。
这是系统性问题,不单单是母亲的问题。
这里包括千百年来谈性色变的“羞耻”烙印。
包括我们文化中的“回避”、“忍耐”、“中庸”、“道德”、“孝顺”、“得体”、“家族荣耀”。
包括上一辈对这种创伤严重程度的认知——他们的“雷达”可能不够敏锐。
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与尊重。
包括他们对处理类似事件的恐惧和耻感。
做鸵鸟便成了父母最常态的选择——“事情或许没有小孩子说的那么严重,即便真的有,少接触就好了,都是一家人/熟人,能怎么办?也没有证据,摸一下不会少一块肉,不声张可能也是保护。”
而母亲作为最先被孩子求助的对象,也没有通过抗争获得解脱的历史经验,曾经也没有人为她们站出来过,她们没有真实需求被看见被满足的熟悉体验。在《夜以继日》里杜俊芳作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外敢打敢拼,给全家带来不错的物质生活。她理解严爱人的梦想,甚至为她牵线,但涉及代表自己形象和切身“利益”的亲生女儿,她是无法欣赏、无法信任、无法鼓励的,她的子女必须“正确”,不能冒进(比如女儿想要学的专业不被允许)。她比上述问题又多了一层家庭关系的“套子”,加上她身上拥有着被亲情塑造后的“钝感”(父母曾经不同意她离婚,那个年代大学生和大学生结婚就应该被羡慕,闹离婚就是笑话,就是不懂事),她的“沉默”便有了和门罗同样可循的原因。
相关小说
- 偷偷看向他
- 偷偷看向他章节目录,提供偷偷看向他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706552字07-21
- 快穿之女人何苦
- 1081543字07-21
- 魂穿小燕子,傻子才甘心等三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瑾怡)的经典小说:《魂穿小燕子,傻子才甘心等三年》最新章...
- 464423字07-23
- 顾总别虐了许小姐嫁给你哥了
- 5755909字07-18
- 揣崽和首长一家下放,被全家团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最爱烧洋竽)的经典小说:《揣崽和首长一家下放,被全家团宠》...
- 578603字07-20
- 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口小月)的经典小说:《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1134522字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