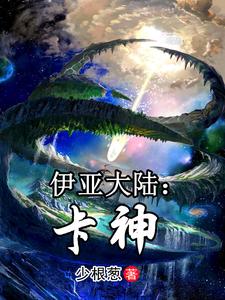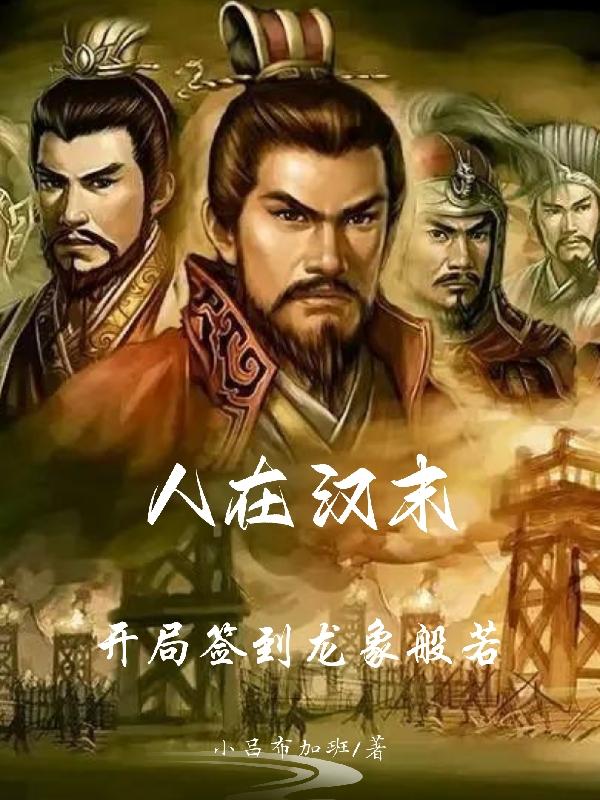第181章 长安城的沉沦,子墨启动布局
长安邓氏别院,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处处彰显着邓氏家族的尊崇。
中堂庭院,八角亭被盈盈碧水环绕,荷叶层层叠叠,似绿绸铺展,娇艳荷花点缀其间,或含苞待放,或肆意盛开。
子墨站在楼台负手而立,轻嗅着荷香,感受着微风拂面的惬意。这宁静优美的景象,却难以抚平他内心的忧虑。
目光悠悠越过远处隐隐约约的秦岭山脉,最终定格在那刚刚升起的朝阳之上。
昨日与长安令杜衡一同巡检长安城的情景,如同一幅幅沉重的画卷,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
长安,这处位于关中平原中心、八水纵横的千年古都,本应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尽享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持续绽放繁华昌盛的光彩。
遥想当年,长安作为大汉的政治文化中心,四方来朝,车水马龙,宫殿巍峨,市井繁华,彰显着泱泱大国的雄浑气魄。
然而如今,黄河及秦岭流域几条河流管理失控,就像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渭河与泾河年年泛滥成灾,浑浊的洪水如猛兽般汹涌,吞噬大片良田。
无数百姓家园被毁,只能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长安城也未能幸免于难,年久失修的城墙,布满斑驳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城门在风雨的侵蚀下摇摇欲坠,再也不见往昔的威严与庄重,全然没了六朝古都的辉煌盛景。
子墨五指紧紧扣住朱漆雕栏,掌下木质裂纹粗糙刺手,那是历史的伤痛,更是这座新贵别院乃至整个长安城衰颓的无声见证,恰似他昨日巡视时所见的凄惨景象:
渭河溃堤之处,浮尸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那是无数鲜活生命消逝的悲怆;
朱雀大街青石板缝里,干涸的流民血迹触目惊心,仿佛在控诉着命运的不公与生活的苦难。
在子墨的记忆深处,东汉时期那位着名水利专家王景,或许是拯救这水患困局的关键所在。
王景治水,采用“堰流法”,修筑了从荥阳到千乘海口长达千余里的黄河大堤,还对汴渠进行了系统整治,使河、汴分流,黄河在之后的八百多年间,大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河道,水患明显减少。
他的治水功绩彪炳史册,可如今,黑木门历经一月有余的苦苦寻觅,却依旧不知其身在何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10页
相关小说
- 全民鬼域:转职天师,招招毁灭级
- 4643479字07-28
- 系统赋我长生,孽徒却要刨我老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太虚雪月)的经典小说:《系统赋我长生,孽徒却要刨我老坟》最...
- 823585字07-29
- 霸天武魂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千里牧尘)的经典小说:《霸天武魂》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1329324字07-26
- 伊亚大陆:卡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少根葱)的经典小说:《伊亚大陆:卡神》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600454字06-29
- 被选中的我们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eFFsTAR)的经典小说:《被选中的我们》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651873字07-29
- 人在汉末:开局签到龙象般若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吕布加班)的经典小说:《人在汉末:开局签到龙象般若》最...
- 2280046字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