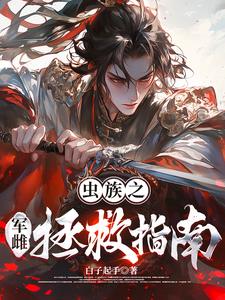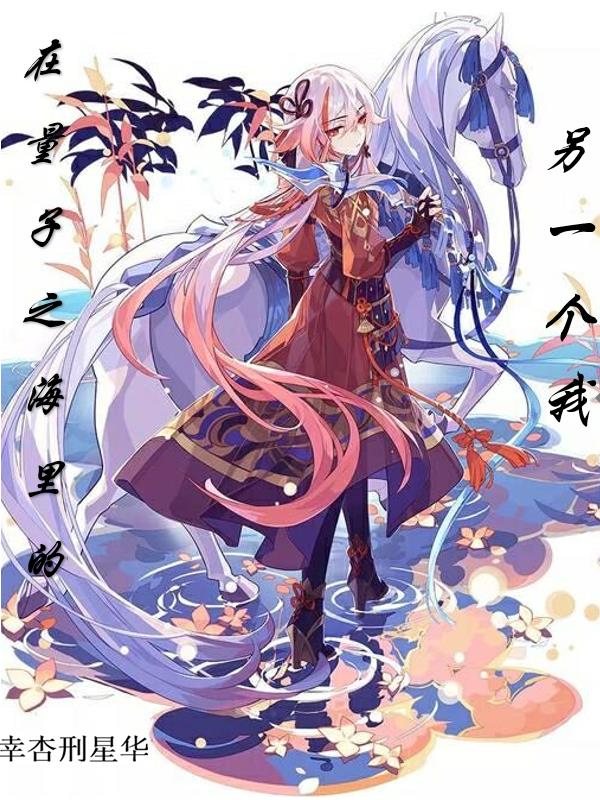第92章 蜀地造物记:从盐井到星穹的匠心长歌
陵江的湾,水流得顺”;就连不起眼的夜壶,也要在底部刻上莲花纹,“粗活里也要有细讲究”。
她的手上总沾着陶土,指甲缝里的泥渍洗不净,却能精准地捏出0.5毫米厚的陶坯。“泥土是活的,你对它好,它就给你长脸。”陈婆婆边揉泥边说,孙女在一旁用手机直播,镜头里,陶轮旋转的轨迹像锦江的漩涡,泥坯在她手中渐渐成型,像一朵慢慢绽放的莲花。有网友留言:“看陈婆婆做陶,像看老成都人泡茶,不急不躁,自有章法。”
荣昌陶的“火气”里,藏着蜀地的包容。明代的“龙纹陶缸”,釉色里掺了重庆綦江的铁矿砂,烧出的红斑像极了川剧脸谱;清代的“渔樵耕读”陶俑,衣纹里能看出蜀锦的褶皱,那是陶艺与织锦的跨时空对话。如今,年轻工匠们把盐井的卤水、峨眉山的竹丝融进陶土,烧出的“新派安陶”,既有老窑的温润,又带着现代的锐气——就像陈婆婆说的:“窑火可以变,泥土的根不能变。”
每年龙窑开窑时,安富镇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村民们捧着自家的陶坯排队,孩子们围着窑口数火舌,陈婆婆则会在第一窑里放一个小小的陶制辣椒:“这是给窑神的见面礼,让他多给咱蜀地的陶添点辣劲。”当通红的陶件从窑中取出,在空气中渐渐冷却,釉色从亮红变成酱紫,像极了川菜里“收汁”的过程——浓油赤酱里,藏着时光的味道。
三、竹编里的草木光阴
青神的竹林,是绿色的海洋。这里的竹篾,能被劈成头发丝般细,却能编出能承重百斤的竹筐;能被拗成九曲十八弯,却始终保持着草木的韧性——就像蜀地的匠人,看似温和,骨子里却藏着宁折不弯的骨气。
王老汉的竹编坊,在竹林深处的茅屋里。他编的竹器,最讲“顺势而为”:楠竹的粗篾编箩筐,要保留竹节的弧度,“这样装谷子才不撒漏”;慈竹的细篾编凉席,要劈成三股交织,“睡上去才不硌人,像躺在云里”;最绝的是他编的“竹丝扣瓷”,竹丝细如蚕丝,紧扣着瓷胎,摇摇晃晃却不掉一丝一毫,“这是咱四川人的‘柔能克刚’”。
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却能把竹篾劈得薄如蝉翼。“竹子有脾气,你得顺着它。”王老汉边劈竹边说,刀刃划过竹青的声音,像春蚕啃食桑叶。有次,一个城里来的年轻人想学编竹篮,急着把竹篾拗成直角,结果断了好几根。“你看这竹林里的竹子,哪根是直挺挺长的?都是弯着绕着往高处长。”王老汉拿起一根弯竹,三下两下编出个圆润的篮底,“做事跟编竹器一样,得懂转弯。”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军雌雌君负面值清除指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子起手)的经典小说:《快穿之军雌雌君负面值清除指南》最...
- 547175字07-14
- 在量子之海里的另一个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幸杏刑星华)的经典小说:《在量子之海里的另一个我》最新章...
- 1014977字07-20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斗罗之冰魔雨浩
- 3740706字06-18
- 崩铁:盘点曝光,原神来碰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吃土豆鸡翅煲的秦风)的经典小说:《崩铁:盘点曝光,原神来...
- 696423字11-28
- HP:当邓布利多有了个女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中浣)的经典小说:《HP:当邓布利多有了个女鹅》最新章节全...
- 680898字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