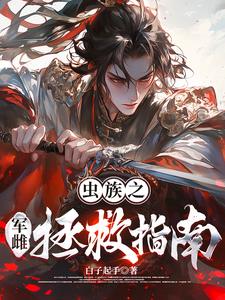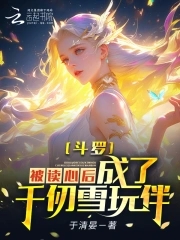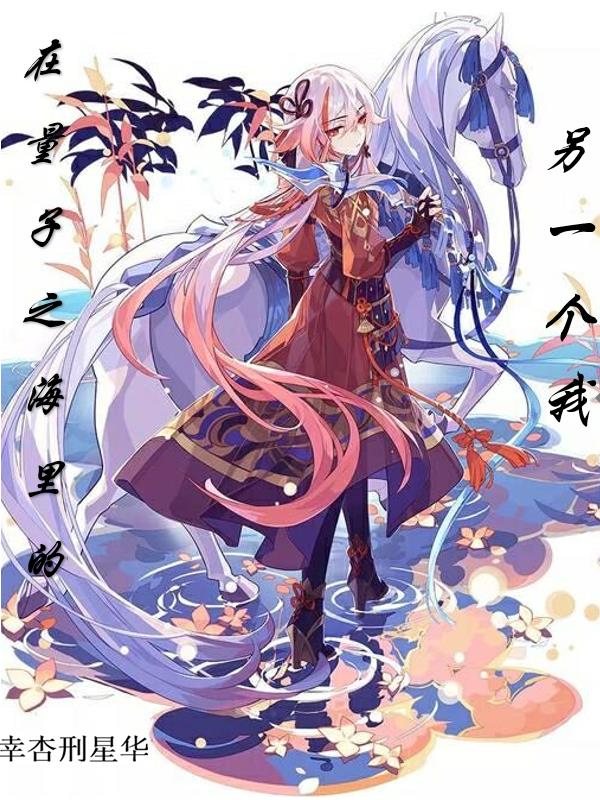第188章 蜀绣:针尖上的千年冠冕
湘绣的“鬅毛针”虽能绣出虎毛的刚劲,却绣不出这种流动的柔;粤绣的“垫绣”追求立体,线条反而显得僵硬。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盖针”是蜀绣的“立体魔法”。先绣一层浅色底,再用深色线在上面交叉覆盖,针脚呈45度角,像给图案打上阴影。绣熊猫时,先用白色丝线铺底,再用灰色盖针绣出背部的绒毛,黑色盖针绣出耳朵,最后用银色线轻轻一点,熊猫的眼睛就活了——那毛茸茸的质感,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摸一摸。成都蜀绣博物馆里有件《猫戏图》,猫爪下的绣球用盖针绣了七层,每层颜色深浅不同,远看像真的有光从球里透出来。这种“分层绣法”,苏绣的“虚实针”只能做到三层,粤绣的“捆咬针”则更侧重线条勾勒,立体效果远不及盖针。
而“衣锦线”的70多道工序,藏着蜀绣的“奢华密码”。将蚕丝线用金箔包裹,再用木槌反复捶打三万次,让金箔与丝线融为一体,制成的线比头发丝还细,却金光闪闪。绣龙袍上的龙纹时,衣锦线要与普通丝线搭配:龙鳞用衣锦线勾勒,龙身用彩线填充,阳光照过时,龙仿佛在绸缎上游动。这门手艺曾是宫廷专属,如今虽已简化工序,却依然保留着“金随丝走,丝伴金辉”的精髓。粤绣虽也常用金银线,但多是直接绣在表面,少了这种“金丝相融”的温润;苏绣、湘绣则极少用金线,奢华感自然稍逊。
针法的巅峰,当属“双面异形异色绣”。一块绸缎,正面绣着红梅傲雪,反面却是白莲映月;正面是飞天的飘带,反面是游鱼的鳞片。最绝的是成都蜀绣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敦煌供养人》:正面是唐代仕女手持莲花,发髻上的珠钗用打籽绣缀满“珍珠”;反面却是西域商人牵着骆驼,骆驼的绒毛用乱针绣得根根分明。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案,全靠绣娘在绸缎中间“暗打结”——针脚从正面看是花瓣的弧度,从反面看却是骆驼的轮廓,丝线的颜色在中间自然过渡,仿佛绸缎里藏着一个折叠的世界。
这门技艺,全国能掌握的绣娘不足十人。蜀绣国家级传承人孟德芝曾演示过:绣一朵正反异色的牡丹,正面用朱砂红,反面用玉色,每绣一针都要计算丝线的走向,确保正面不露反面的色,反面不显正面的针。她算过,每绣一平方厘米,就要耗费三个小时,比苏绣的双面绣费时十倍,比粤绣的异色绣复杂百倍。湘绣虽以单面立体见长,却从未涉足双面异形的领域。这种“在矛盾中求和谐”的技艺,让蜀绣站在了中国刺绣的巅峰。
三、丝绸上的蜀地风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军雌雌君负面值清除指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子起手)的经典小说:《快穿之军雌雌君负面值清除指南》最...
- 547175字07-14
- 斗罗:被读心后,成为千仞雪玩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于清晏)的经典小说:《斗罗:被读心后,成为千仞雪玩伴》最新...
- 436265字07-20
- 在量子之海里的另一个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幸杏刑星华)的经典小说:《在量子之海里的另一个我》最新章...
- 1014977字07-20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斗罗二:获得系统后我成了万人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弓长离歌)的经典小说:《斗罗二:获得系统后我成了万人迷》...
- 403403字11-30
- 斗罗之冰魔雨浩
- 3740706字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