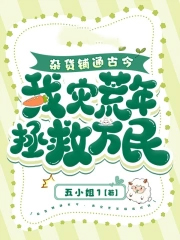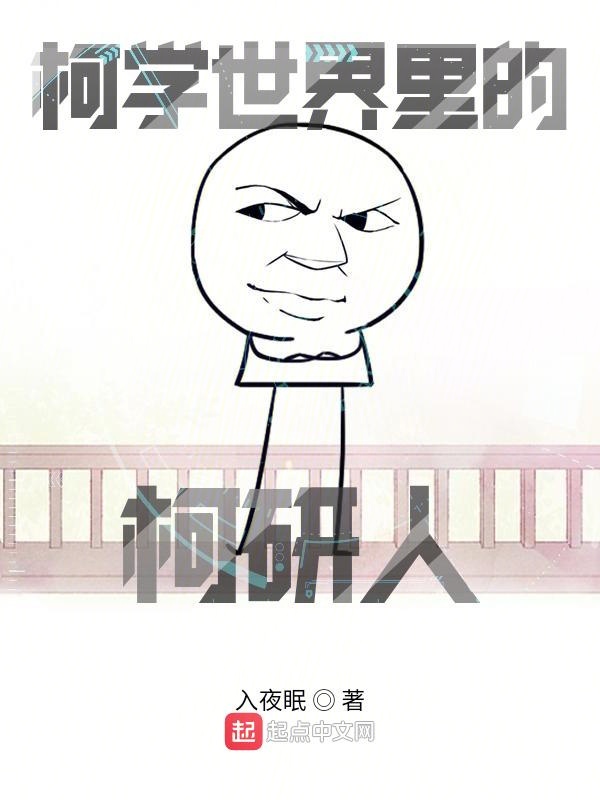第188章 蜀绣:针尖上的千年冠冕
那时的成都绣巷从浣花溪延伸到九眼桥,清晨晾晒的绣品堆得像云霞,牡丹用平针铺底,芙蓉用滚针勾边,连路过的波斯商人都忍不住用银币换一块绣着“联珠纹”的手帕。而此时的苏绣,才刚在苏州出现零星的绣坊;粤绣要等到明清海禁开放后,才借着外贸的东风兴盛起来。
明清的蜀绣,早已是寻常百姓的日子。成都青石桥一带的“绣户”,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摆着绣绷:母亲教女儿绣“鸳鸯戏水”,针脚要顺着水流的方向走;婆婆为媳妇绣“麒麟送子”,麒麟的鳞片要用打籽绣一粒粒缀满;孩童周岁的肚兜上,必定绣着“长命锁”,锁扣处用双线绣出“卍”字纹。清代《成都通览》记载,成都城内“绣坊百余家,绣娘数千人”,连挑担卖花的小贩,担子上都盖着块绣着月季的布帘——蜀绣不是高高在上的技艺,而是融进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这种“从庙堂到江湖”的完整传承链,是其他绣种难以比拟的:苏绣虽在明清达到巅峰,却始终带着文人雅士的清高;粤绣依赖贡品与外贸,少了几分市井温情;湘绣直到清末才形成风格,历史的厚度终究稍逊。
二、130种针法的万象世界
蜀绣的妙,在针脚里藏着宇宙。当苏绣用30余种针法勾勒江南烟雨,粤绣以50余种针法堆砌岭南浓艳,湘绣凭70余种针法塑造楚地雄风时,蜀绣已用12大类130余种针法,织就了一部刺绣的“百科全书”。老绣娘常说:“天地有阴阳,针法有刚柔,万物皆可绣,全看针怎么走。”
最基础的“铺针”,是蜀绣的“地基”。绣娘将丝线在绸缎上平铺,针脚长短一致如列队的士兵,给图案铺一层均匀的底色。绣大面积的山水时,铺针要顺着山势的起伏走,像给山峦盖上一层薄被;绣湖面时则要水平排列,让绸缎泛起水波的光泽。学绣的第一步就是练铺针,新徒弟常常绣得歪歪扭扭,师傅便让她们先在纸上画直线,画到手腕稳了,再拿针——这一练,往往就是半年。苏绣也有类似的“平针”,但针脚偏短偏密,更适合绣纤细的花鸟;蜀绣的铺针则可长可短,既能绣出芙蓉花瓣的饱满,也能绣出竹叶的修长。
“滚针”是蜀绣的“流动密码”。针脚像水波一样层层推进,每一针都压住上一针的一半,绣出来的线条圆润如珠,最适合绣龙的胡须、水的波纹。清代蜀绣珍品《蛟龙出海图》里,龙的胡须用滚针绣就,长近半米,却没有一处断裂,远看像真的在风中飘动。绣娘说,绣滚针要“心随针走,手随心动”,急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得像锦江的水,不急不缓自有韵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地球神话人物,在星际炸裂
- 地球神话人物,在星际炸裂章节目录,提供地球神话人物,在星际炸裂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83077字06-08
- 杂货铺通古今,我灾荒年拯救万民
- 杂货铺通古今,我灾荒年拯救万民章节目录,提供杂货铺通古今,我灾荒年拯救万民的最新...
- 640573字07-17
- 诸天万界之大拯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放羊小星星)的经典小说:《诸天万界之大拯救》最新章节全文...
- 11815790字07-20
- 斗破之无上之境
- 你常说,复仇才是我的使命,但你却不知道,守护你,才是我一生的宿命等级制度:斗帝、...
- 15115643字06-25
- 柯学世界里的柯研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入夜眠)的经典小说:《柯学世界里的柯研人》最新章节全文阅...
- 9096479字07-11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