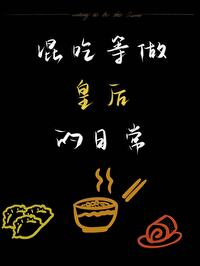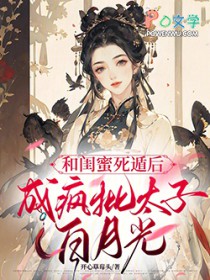第185章 北纬30:巴蜀奇景与世界谜团的交织
斯科岩画则是"跨越时空的喊话"。考古学家在岩画旁发现了1.7万年前的脚印,有大人的,也有小孩的,脚趾印很深,像是踮着脚在看。岩壁上的手印不是完整的,只有四根手指——古人为了把自己的存在刻进石头,故意蜷起小指,像在说:"我来过,我看见过。"更妙的是,他们画的野牛肚子里,藏着用白色颜料勾勒的小野牛,像是在预言:"现在是冬天,春天会有新生命。"
人与光亮的相处也大相径庭。黄龙洞的向导从不用手电筒直射蝙蝠,他们把光打在岩壁上,让反射的微光照亮路——"要给它们留暗处,就像客人来了,得留间房。"拉斯科洞穴现在被关闭了,游客只能看复制品,因为现代人的呼吸会让岩壁发霉,那些远古的星光正在慢慢褪色。老杨听说后直摇头:"我们彝人进洞,会带块松脂,只在必要时点亮,看完就吹灭,石头也要喘气的。"
当我们在黄龙洞看到荧光蝙蝠掠过钟乳石,突然明白:有些黑暗里的光亮,不需要被全世界看见。它们只在该亮的时候亮,该暗的时候暗,像守着一个古老的约定。
三、汉水源的漩涡与耶路撒冷的石头:信仰的模样
汉水源的漩涡总在旋转,像个永远解不开的结。站在岸边看,水面的漩涡直径五米,顺时针转得均匀,像钟表的指针,可水下三米处,暗流却在逆时针转,把投入的树枝拧成麻花。老羌是守潭人,他爷爷曾在漩涡边捡到块带字的砖,"上面的字像水波,认不全,只看出个'羌'字"。现在那块砖被他锁在木箱里,初一十五拿出来擦一擦,砖缝里总渗出清水,擦不干。
耶路撒冷的石头则记着太多故事。哭墙的石缝里塞满了纸条,有希伯来语的祈祷,也有中文的心愿,石头被摸得发亮,像无数只眼睛在看。1967年,以色列士兵夺回老城时,对着哭墙哭了整整一夜,他们的眼泪渗进石缝,与两千年前犹太人的眼泪混在一起。
两种信仰,长在不同的土壤里。 汉水源的漩涡从不被看作"神迹",而是"提醒"。老羌说:"祖先治水时留下的,转得快了,就是要下雨;转得慢了,就得防旱。"每年端午,他会带着族人往漩涡里投米,不是祭祀,"是告诉祖先,今年的收成够吃,不用操心"。他们的信仰里没有恐惧,只有像家人一样的叮嘱。去年大旱,漩涡转得慢如蜗牛,老羌组织人疏通上游的河道,果然三天后下了雨,"漩涡就是个活的晴雨表,你对它好,它就提醒你"。
耶路撒冷的石头则浸满了冲突与和解。哭墙属于犹太人,墙的另一边是穆斯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
- 2740951字07-19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章节目录,提供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808924字07-18
- 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
- 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章节目录,提供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476108字07-18
- 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
- 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章节目录,提供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的最新...
- 762398字07-18
- 恶毒女配,但创飞剧情
- 恶毒女配,但创飞剧情章节目录,提供恶毒女配,但创飞剧情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810145字07-18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75/62775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