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剑笔同辉:张爱萍诗词里的山河与锋芒
一、少年笔作龙泉剑
1925年的达州城,州河的水裹挟着泥沙奔涌。15岁的张爱萍站在达县中学操场的石阶上,手里攥着刚写好的传单,纸角被汗水浸得发皱。当"唤起民众齐奋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句子从他喉咙里迸发出来时,秋风突然卷起传单,像一群白色的鸟掠过围观者的头顶。这是他第一次把文字当作武器,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诗,只觉得这些字能像石头砸向那些欺负人的家伙。"
川东的私塾先生曾教他"文以载道",可他见过地主的皮鞭抽在佃户王大爷身上,见过外国商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把渔船撞翻。在达县中学的煤油灯下,他把《新青年》的文章抄在田字格本上,旁边却画满了步枪和大刀。有次作文课,先生让写《我的志向》,他挥笔而就:"州河从此狂怒吼,踏着血迹救中华",墨迹穿透了纸背,惊得先生半晌说不出话。先生后来找到他,摸着他的头叹:"你这字里有杀气,也有正气。"
1929年的上海,法租界的梧桐叶落在他被捕时穿的蓝布长衫上。提篮桥西牢的铁窗漏进一点微光,照亮他在墙壁上刻下的句子:"泥城桥前洋奴棍,西牢楼中好汉强"。狱卒以为他在发疯,用枪托砸他的手,他却笑着往墙上啐了口血:"越砸,这字越结实。"牢房里阴暗潮湿,他就借着每天半小时的放风时间,把脑子里的句子默记在心里。有次放风时,他看见墙外的桃花开了,当即想出"铁窗锁不住春光",回来就着墙壁的潮气写下来,怕忘了。
第二次入狱时,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墙缝里渗着寒气。同牢的难友是位老秀才,见他总在烟盒纸上写东西,便教他平仄对仗。在老秀才的指点下,他把"申江怒涛"改成"申江怒涛拍天浪",说这样"更有劲儿"。出狱那天正赶上寒潮,他裹着单薄的囚衣走在苏州河畔,却觉得心里烧得慌,掏出藏在鞋底的半截铅笔,在桥洞下写下:"朔风凛冽夜肃煞,浪迹姑苏何处家。回溯申江觅源处,源头自有艳阳花。"写完把纸叠成小船放进河里,看着它漂向远方,像目送一个不会沉没的希望。
多年后整理旧物,家人发现他青年时期的笔记本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梧桐叶,叶面上用铅笔写着半阙残诗:"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笔迹稚嫩却带着股狠劲,像极了他第一次握枪时,在靶纸上打出的歪歪扭扭的弹孔。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枝笔和这柄枪,会伴随他走过大半个中国,写出比诗句更壮阔的人生。
二、马背诗吟烽火路
1935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别人朝我扔泥巴躺下讹他三万八
- 别人朝我扔泥巴躺下讹他三万八章节目录,提供别人朝我扔泥巴躺下讹他三万八的最新更...
- 2498083字07-18
- 我有一本穿越者攻略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立川页)的经典小说:《我有一本穿越者攻略》最新章节全文阅...
- 767638字07-19
- 重生樱木的逆天征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听涛的憨猫)的经典小说:《重生樱木的逆天征途》最新章节全...
- 561049字07-13
- 我在贵族学院当班长[穿书]
- 888163字07-13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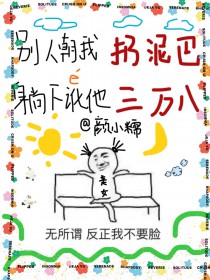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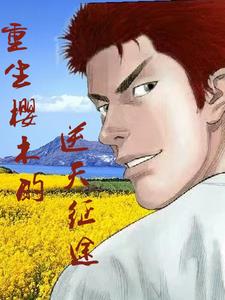
![我在贵族学院当班长[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0/60661/60661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