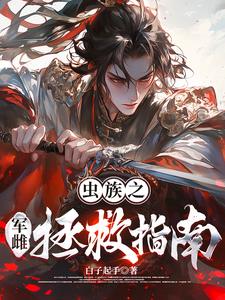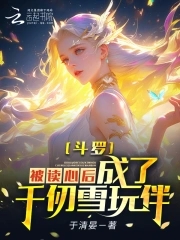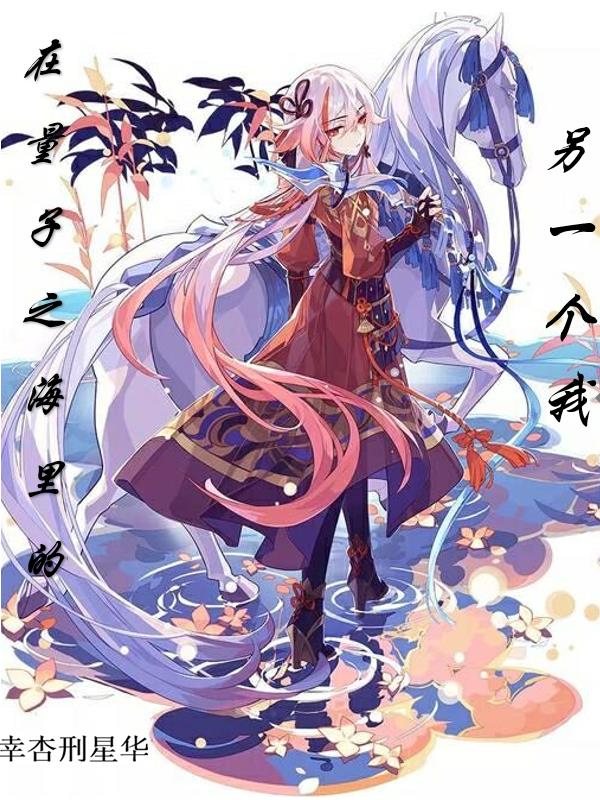第182章 巴蜀烟盒里的旧时光
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父亲是1982年进的建筑队,在攀枝花修钢厂时,兜里揣的永远是工字牌。他说,那时候的工人认死理:“工字牌,工人的牌,抽着踏实。”烟盒是软纸的,边角总被汗水浸得发皱,却被手心的温度焐得平整。下工后,几个人蹲在脚手架下,烟在指间传,一口烟一口粗茶,烟丝燃着的“滋滋”声,比水泥搅拌机还动听。
有次父亲发高烧,师傅从怀里掏出支工字牌,烟盒都被体温焐软了。“抽口,发发汗就好了。”师傅说。烟味呛得父亲眼泪直流,咳嗽声震得工棚的木板响,病竟真的好了大半。后来那师傅退休,父亲特意托人买了两条工字牌送他,两人坐在拆下来的脚手架上,对着烟盒喝了一下午酒,说的都是哪个桥墩难打,哪个大梁难架,烟蒂扔了一地,像撒了把钉子。
工字牌的烟丝,是用什邡的好叶子做的。老烟民一抽就知道:“叶片宽,烤得透,烟灰白得像雪。”父亲说,那时候的烟厂就在什邡,烟丝都是工人用竹筛子筛过的,连碎末都少见。有年烟厂的人来工地调研,父亲还提过建议:“把‘工’字再刻深点,显得有力量。”
工字牌的退场,像老建筑的拆除。90年代末,工地上的烟越来越花哨,过滤嘴越来越长,烟盒上印着明星和跑车。年轻工人说:“工字牌太糙,拿不出手。”父亲整理旧物时,翻出个铁皮烟盒,里面还剩半包发黄的工字烟,烟丝硬得像枯草。他捏起一支,对着光看了很久,“这烟丝,当年能看见叶脉”。
烟早抽不了了,但那“工”字,像枚生了锈的勋章,别在岁月的衣襟上。去年父亲去攀枝花参加厂庆,遇见当年的师傅,师傅从兜里掏出个塑封的工字烟盒,“一直留着,看见它,就想起你们这帮小子抢烟抽的样”。两个老头对着烟盒笑,眼角的皱纹里,还藏着当年工地上的风。
四、山城的雾散了,码头边的剪影
山城牌的烟盒上,永远印着解放碑的剪影。碑身尖尖的,直插烟盒顶端,周围绕着几缕灰雾,像重庆码头的晨雾,朦胧得恰到好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庆,这抹剪影是街头巷尾的“城标”——挑夫的扁担上挂着,老板的抽屉里躺着,甚至公交车的扶手上,都能看见有人夹着支山城烟,烟盒边角被摩挲得发亮。
外公是朝天门码头的“棒棒”,他的竹筐柄上总缠着圈绳子,绳子上挂着个铁皮烟盒,里面装的永远是山城牌。“抽口山城,才算回了家。”他说。烟盒上的解放碑,被他的拇指磨得有些模糊,碑底的“重庆”二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军雌雌君负面值清除指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子起手)的经典小说:《快穿之军雌雌君负面值清除指南》最...
- 547175字07-14
- 斗罗:被读心后,成为千仞雪玩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于清晏)的经典小说:《斗罗:被读心后,成为千仞雪玩伴》最新...
- 436265字07-20
- 在量子之海里的另一个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幸杏刑星华)的经典小说:《在量子之海里的另一个我》最新章...
- 1014977字07-20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斗罗二:获得系统后我成了万人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弓长离歌)的经典小说:《斗罗二:获得系统后我成了万人迷》...
- 403403字11-30
- 斗罗之冰魔雨浩
- 3740706字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