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四川话里的儿:舌尖上的小团圆
四川话的儿化音,不像北京话那样卷得利落,也不似东北话那样带着股子敞亮的劲儿。它更像成都茶馆里泡软了的碧潭飘雪,轻轻巧巧落在舌尖,打个转儿就化了,留下点温温柔柔的余味。你听嘛,黄豆不叫黄豆,得叫“黄豆儿”;绿豆不叫绿豆,得叫“绿豆儿”;就连最普通的碗,也要添个“儿”,成了“碗儿”——仿佛不加这个小尾巴,物件就少了点烟火气,生分了似的。
一、豆荚里滚出来的“儿”
菜市场的摊摊上,最先听出四川话的温柔。卖干货的张嬢嬢掀开竹簸箕,里头的豆子滚得叮当作响,她操着带点鼻音的成都话招呼:“看下嘛,新收的黄豆儿,打豆浆巴适得板!”“豆”字刚落,舌尖轻轻一翘,“儿”就跟着溜出来了,软乎乎的,像豆子在簸箕里打了个滚。
旁边堆着的绿豆,绿得发亮,张嬢嬢抓起一把,指缝里漏下几颗:“绿豆儿熬稀饭,清热得很,给娃娃多吃点。”这“绿豆儿”的“儿”,比“黄豆儿”更轻,几乎要和“豆”字粘在一起,像绿豆壳上那层薄薄的膜,不仔细听,还以为是豆子自己在喘气。
四川人对豆子的“儿化”,像是给每颗豆子起了小名。红豆叫“红豆儿”,煮粥时妈妈会念叨:“红豆儿要提前泡,不然煮不烂。”赤小豆个头小,就叫“赤小豆儿”,加个“儿”,仿佛个头又小了一圈,更让人疼惜。连最不起眼的豇豆,嫩的时候也得叫“豇豆儿”,炒之前掐掉头尾,“豇豆儿要切短点,不然夹不起”——仿佛不加“儿”,豇豆就会长得没个分寸,横冲直撞地躺在盘子里。
我小时候蹲在灶台边看奶奶捡豆子,她捏起颗坏了的黄豆,皱着眉丢进垃圾桶:“这个黄豆儿遭虫蛀了,不能要。”又捡起颗饱满的绿豆,放在手心里转:“你看这个绿豆儿,圆滚滚的,像不像你眼睛?”我盯着她手心的绿豆,忽然觉得那“儿”字像层光晕,把豆子照得暖融融的。后来才明白,四川人给豆子加“儿”,哪是单纯的发音习惯,分明是把这些土里长出来的物件,当成了家里的一份子,带着点“自己人”的亲昵。
有次在乡下,听见老农跟收购商讨价还价:“你这个价太低了,我这黄豆儿晒得干,颗颗饱满,加两毛嘛!”那“黄豆儿”三个字,说得又重又软,重的是底气,软的是对豆子的心疼。收购商被说动了,笑着说:“看在你这黄豆儿长得乖的份上,加一毛。”——你看,连讨价还价都带着对“豆儿”的夸奖,仿佛豆子听得懂人话,会因为这声“儿”而更香甜些。
二、娃字后面的“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别人朝我扔泥巴躺下讹他三万八
- 别人朝我扔泥巴躺下讹他三万八章节目录,提供别人朝我扔泥巴躺下讹他三万八的最新更...
- 2498083字07-18
- 我有一本穿越者攻略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立川页)的经典小说:《我有一本穿越者攻略》最新章节全文阅...
- 767638字07-19
- 重生樱木的逆天征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听涛的憨猫)的经典小说:《重生樱木的逆天征途》最新章节全...
- 561049字07-13
- 我在贵族学院当班长[穿书]
- 888163字07-13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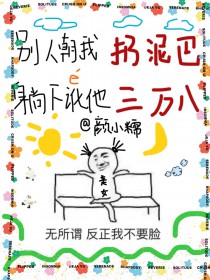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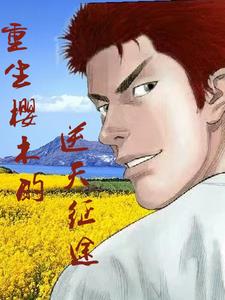
![我在贵族学院当班长[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0/60661/60661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