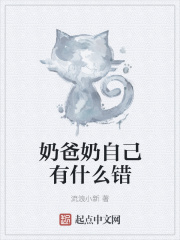第158章 钢与柔:成都东郊的双重叙事
鸣,烟囱喘息,还有那些永不褪色的烟火气。
王婆婆最近总爱往东郊记忆跑,不是为了看年轻人的热闹,而是去漫卡街的修表铺。铺子老板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却能修好她那块上海牌手表——那是1970年厂里发的先进奖品,表蒙子上的划痕比她脸上的皱纹还多。"小伙子,你这手艺跟当年厂里的张师傅有得一拼。"王婆婆边说边从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她攒的糖块,"尝尝,当年厂里发的水果糖,跟现在的不一样。"年轻人笑着接过来,说:"婆婆,您这表修好了能当展品了,好多游客都想拍它呢。"
上个月厂庆,东郊记忆搞了场"师徒见面会"。老郑师傅的徒弟小李特意从深圳回来,带着他现在公司生产的智能手表,跟师傅的老工具包摆在一起。"师傅,当年您教我磨刀具的法子,我现在教徒弟编程都在用——耐心比啥都重要。"小李说着,给师傅鞠了个躬,老郑师傅抹了把眼睛,从工具包里掏出个用油布包着的东西,是枚磨得发亮的刀片:"给,你当年总说想要我这把'看家刀',现在给你。"周围的老工人们都红了眼眶,年轻人们举着相机,把这一幕定格成永恒。
贸易公司的旧址现在成了文创书店,玻璃柜台里摆着的不再是花布肥皂,而是印着老厂房图案的笔记本。我挑了本封面上有106信箱的本子,收银台的姑娘笑着说:"好多红光厂的老人来买这个,说要给孙子写故事。"书架上还摆着本《红光电子管厂史》,翻开第一页,就是那张苏联专家和工人一起举着示波管的老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还很年轻,笑容比阳光还灿烂。
有天清晨,我又遇见老陈在修那辆773厂的通勤车。车把上的红绸子被风吹得飘起来,像面小小的红旗。"今天要去参加幼儿园的活动,"他笑着说,"现在的幼儿园就在当年厂里的幼儿园旧址,我带这车去给孩子们讲讲过去的事。"车铃铛"叮铃铃"响起来,惊飞了铁轨边的麻雀,它们扑棱棱地飞向天空,翅膀掠过东郊记忆的玻璃幕墙,映出老厂房和新高楼重叠的影子。
夕阳西下时,我站在半截烟囱下,看着晚霞把红砖染成金色。远处传来livehouse的歌声,混着老茶馆里的川剧唱腔,像首跨越时空的二重唱。有个穿工装的雕塑立在广场中央,手里举着示波管,管身上反射着现代建筑的光,像把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钥匙。
东郊的故事,从来就没结束过。那些车床的轰鸣变成了歌声,那些烟囱的呼吸变成了笑声,那些藏在信箱里的秘密,变成了挂在墙上的老照片。而我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13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八零,让我过继你们又后悔什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幺呦)的经典小说:《八零,让我过继你们又后悔什么?》最新章...
- 295973字07-28
- 傻白甜美人重生后杀疯了
- 1104524字04-23
- 女配在七零[穿书]
- 女配在七零[穿书]章节目录,提供女配在七零[穿书]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014473字07-26
- 奶爸奶自己有什么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流浪小新)的经典小说:《奶爸奶自己有什么错》最新章节全文...
- 2537405字07-25
- 穿成豪门亲妈我哈哈哈哈哈哈
- 1383962字0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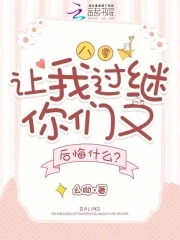

![女配在七零[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5/65857/65857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