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 戴安娜牛排
('\n
余嘉鸿转头问:“美月表姐,肯定要建禁闭式难民营吗?”
\n
“没办法,”蔡美月放下筷子,“现在越南的人均年收入也就150到200美元左右,一个月算下来不过12到17美元。但你看看港城,码头工人月薪都有1500港币,相当于越南人干一整年的收入。政治难民里混着不少人,说是逃难,眼睛却盯着港城的霓虹灯。在他们心里,香港街头捡垃圾都能发财。”
\n
炭火在陶盆下噼啪作响,鲍汁的香气裹着蒸汽升腾。蔡美月夹起一块鲍鱼:“所以不允许外出工作,还要用禁闭式营区限制自由,这不是狠心,是吓阻。你想啊,一个越南渔民在海上漂一个月,冒死到港城,结果发现不能打工、不能随便出门,跟蹲监狱似的,下次还会有人愿意来吗?港城的善意也一样,得有个度,不然就成了吸引苍蝇的臭肉。”
\n
“可这样会不会误伤真的走投无路的人?”岳宁忍不住问。
\n
蔡美月叹了口气:“所以才叫‘合乎人道的阻吓’,该救的人要救,可有人为了来港城,故意把船凿个洞,说是‘逃难’,其实是算准了港府不敢见死不救。建禁闭式营区,对真难民是苦了点,但至少能让他们等到去第三国的船票;对那些想混进来赚钱的人,也算断了念想。”
\n
蔡美月介绍起港府的设想,初期用两所旧监狱改造成难民营,新到达的难民必须住在禁闭式难民营内。
\n
“我见过的难民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上海的南市难民营。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大量人员涌入上海,想要进入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关闭了入口,把难民堵在了租界之外。法国神父主持开设了南市难民营,收留了三十五万难民。里面秩序井然,有学堂和医院,也有工厂。我就是在南市难民营遇到了宝如。”
\n
“是啊!我刚开始在一个中国人开的难民营,那里就是等着饿死,后来哥哥把我们送到了何神父那里,医生给我们治病,尼姑庵的师太照顾我们。”三舅妈李向好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疯玩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自在悠闲)的经典小说:《疯玩之旅》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776896字07-12
- 人皇天帝
- 49956字07-15
- 麒麟出世,师父让我下山去结婚
- 1266061字07-15
- 邪神伪装玩家后[无限]
- 925331字07-15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811279字07-03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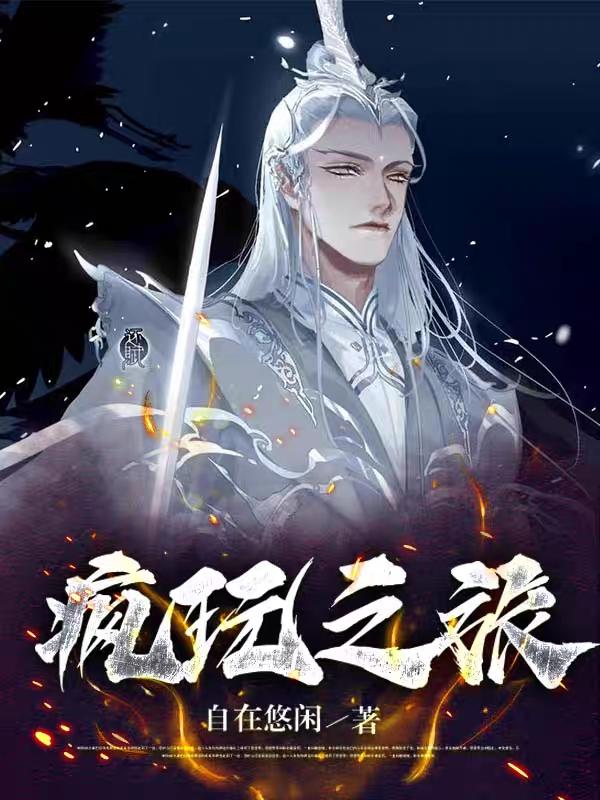


![邪神伪装玩家后[无限]](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1/61195/61195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