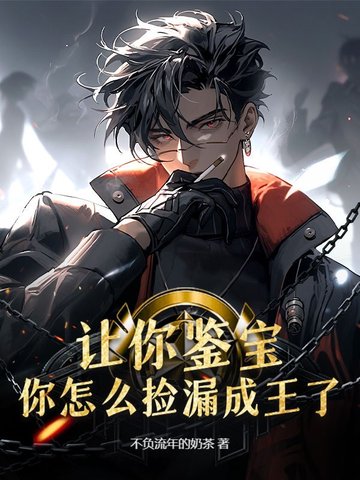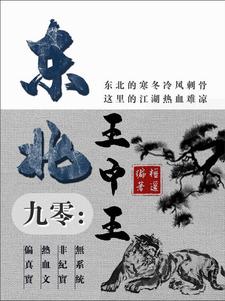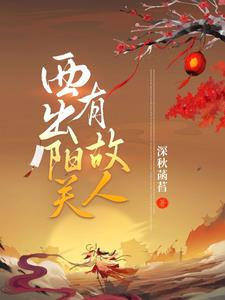第4章 惊世之辩与青史留笔
摘下眼镜擦拭:“你这理论超前了至少五年,立法能跟得上吗?”
祁同伟迎上恩师的目光,想起三年前在孤鹰岭煤炉前煮挂面的夜晚:
“老师,1979 年刑法连‘计算机犯罪’都没写,可现在呢?立法不是跟在犯罪屁股后面跑,是要像警灯一样,提前照亮黑暗的角落。”
答辩通过的第三天,《现代刑事侦查方法论新探》与《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与预防》在公安大学出版社上架。
首印五千册三天售罄,新华书店的销售员打电话来:“你们这书邪门了,穿警服的抢着买,还有人拿 BP 机号排队预定!”
真正的风暴始于公安部内部会议。
某副局长在全国刑侦工作会上拍了桌子:“祁同伟说我们‘重口供轻物证’?1998 年全国命案破案率 89%,他一个书生懂个啥!”
话音未落,王老拄着拐杖站起来:“1996 年石家庄爆炸案,要不是现场勘查漏了半枚指纹,能拖三个月?小祁书里写的‘微量物证七步法’,我让部里试过,上个月破的碎尸案就靠头发丝里的油漆成分定的罪!”
更棘手的麻烦来自学术界。
某老牌刑侦专家在《人民公安报》撰文:“搞理论的别瞎指挥,什么‘行为证据学’,有我们老侦察员的‘望闻问切’好使?”
祁同伟没动笔反驳,只是带着书去了西城分局刑警队。
当他用 “犯罪惯技分析” 还原出系列盗窃案嫌疑人的职业特征(送奶工),队长拍着他的肩膀:“祁博士,那专家要敢来,我拿案卷砸他脸!”
最让他心惊的是匿名举报信。
有人寄到公安部纪委,说他 “抄袭国外理论”“借出书捞取名利”。
1999 年国庆前夕,教育部突然下文,将两本书列为全国公安院校必读书。
消息传来时,祁同伟正在王老办公室整理新课题。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个红绸布包:“这是 1952 年我参加镇压反革命时的笔记本,里面记着枪毙特务的流程。小祁啊,你写书是用笔杆子革命,但笔杆子要硬,得有枪杆子护着。”
他打开布包,里面是本牛皮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用钢笔写着:“1953 年 1 月 7 日,审讯敌特王某,其妻携子来探监,王某当场崩溃交代……”
祁同伟忽然明白,王老让他参与 “职务犯罪心理” 课题,不是搞学术,是在教他看权力场的人心鬼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公子下班了)的经典小说:《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452867字05-05
- 追燕
- 505604字09-10
- 敢爬墙就操死(1v2)
- 566193字12-22
- 让你鉴宝,你怎么捡漏成王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不负流年的奶茶)的经典小说:《让你鉴宝,你怎么捡漏成王了?...
- 408806字07-14
- 九零:东北风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梧遥)的经典小说:《九零:东北风云》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8056880字09-11
- 西出阳关有故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深秋菡萏)的经典小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772204字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