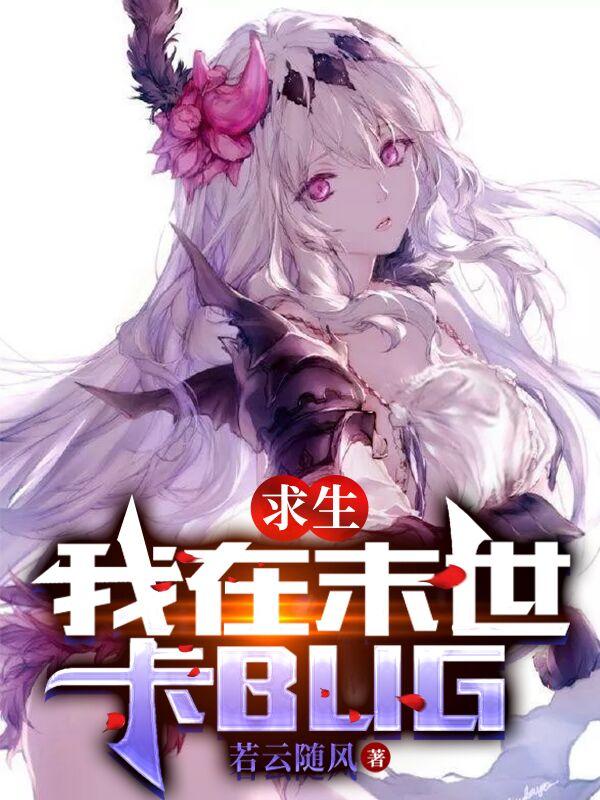第52章 赤土哀歌
陋的工具甚至双手,一点点刨开坚硬如铁的地表,试图播下从废墟中翻找出的、不知能否存活的种子。渴了,只能冒险去锈河边汲取那浑浊的、蕴含未知危险的河水。饥饿和疾病如同跗骨之蛆,带走一个又一个同伴。变异生物的零星袭击,更是雪上加霜。
但人,终究是顽强的。
一代又一代的挣扎求生,如同愚公移山。失败的经验累积成教训,偶然发现的、能在赤土上顽强存活的变异植物(比如最初形态的铁皮土豆)成为了希望的种子。微小的绿点,开始在无边赤红中艰难地、零星地出现。它们脆弱,产量低得可怜,却代表着活下去的可能。
人口,在绝望的夹缝中,如同野草般缓慢而坚韧地增长。分散的、微小的聚居点,如同赤土上的疮疤,渐渐多了起来。人们互通有无,交换着在赤土上挣扎求生的微末经验,形成了最原始、最脆弱的互助网络。赤土,这片被诅咒的土地,竟也因这些被遗忘者的聚集,透出了一丝微弱的人气。
这微弱的人气,终于引起了高高在上的“官方”生存基地的注意。
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冰冷的计算。
在废土世界,人口本身就是资源——劳动力资源、兵源、以及潜在的实验样本资源。尤其是当这些人口在赤土这种公认的绝地上,竟然能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并初步摸索出一些在污染土地上种植变异作物的方法时,其“研究价值”和“边际效益”就被纳入了官方的评估体系。
于是,代表“秩序”与“管理”的触角,伸向了这片赤土。
在赤土流民聚居相对集中的区域边缘,靠近锈河一条相对平缓的支流拐弯处,一座冰冷的钢铁哨站拔地而起。随后,高耸的、带有高压电防护网和自动防御炮塔的合金围墙开始圈地。大型工程机械在武装人员的护卫下轰鸣进场,粗暴地推平了流民们辛苦开垦出的小片田地,夷平了那些摇摇欲坠的窝棚。
“0号种植基地”——这个带着强烈试验性和编号意味的名字,被刻印在合金大门冰冷的铭牌上。
基地的建立,对赤土流民而言,是福祸相依的双刃剑。
“福”在于,基地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秩序(以高压手段维持),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基础医疗和净化水供应点(需要高昂的贡献点兑换),以及……一个名义上的“庇护”。基地外围的巡逻队和防御设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驱逐了大型的、成群的污染兽,让流民们夜晚睡觉时不必再担心被拖走吃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直击人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有钱我有颜)的经典小说:《直击人性》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190459字06-27
- 求生:我在末世卡BUG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若云随风)的经典小说:《求生:我在末世卡BUG》最新章节全文...
- 2196944字07-12
- 崩坏:崩崩崩全崩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心梦化蓝图)的经典小说:《崩坏:崩崩崩全崩了》最新章节全...
- 559448字07-18
- 热血传奇:天灾道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头顽童)的经典小说:《热血传奇:天灾道主》最新章节全文...
- 868128字07-19
- 镇魂街:群英唐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熊熊不怕黑)的经典小说:《镇魂街:群英唐王》最新章节全文...
- 975276字07-13
- 小马宝莉逐梦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是风华呀)的经典小说:《小马宝莉逐梦之旅》最新章节全文阅...
- 562331字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