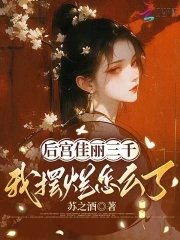第129章 雨靴水痕在地面的抽象构成
精彩!
于是,在雨后初晴的街道上,一个穿着西装的建筑师和一个提着陶土工具包的陶艺家,开始以一种近乎孩童的方式行走。他们不看地面,任由雨靴随机踩进积水里,溅起的水花在裤脚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赵环能感觉到鞋底与地面接触时的不同阻力——踩在光滑的瓷砖上是一种反馈,碾过粗糙的沥青又是另一种质感,这让他想起郭静描述的“揉泥时手掌对泥土颗粒的感知”。
走到街区尽头,他们同时回头。身后的地面上,两道交错的水痕轨迹蜿蜒伸展,赵环的脚印相对规整,带着不自觉的平行倾向,而郭静的则充满了突然的转折和自由的弧线,偶尔有几个深凹的印记,显然是她故意用力踩下的结果。最奇妙的是,在某些节点,两人的脚印重叠或相切,形成了类似建筑图纸上“节点大样”的复杂图案。
“像不像你设计的那个螺旋楼梯?”郭静指着一处两人脚印交汇的地方,那里的水痕形成了一个不完整的螺旋,“但多了些泥土的颗粒感。”
赵环拿出手机拍照,镜头下的水痕图案在阳光下逐渐变淡,如同正在消失的临时雕塑。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为一个展览设计的“消失的建筑”概念,用可降解材料搭建的结构,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融入自然。而眼前的水痕,正是这种概念的完美诠释——建筑的临时性与陶艺的瞬间性在此刻达成了共振。
“应该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郭静从包里拿出速写本,不是画下最终的图案,而是开始记录行走时的感觉:“第七步,左脚踩进一个较深的水坑,水花溅到小腿,凉意从胫骨传导到膝盖,像揉泥时突然触到一块湿度不均的陶土。”
赵环受到启发,也在平板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档:“第十五步,右脚踩在两块地砖的接缝处,水痕向两侧分流,角度约72度,这让我想起拱券结构的应力分布,但更自由。”
他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记录,将身体的触觉、视觉的印象、职业的联想转化为文字和草图。当他们回到咖啡馆取遗忘的雨伞时,店员正用拖把清理地面,那些他们曾仔细观察的水痕正在被抹去,如同从未存在过。
“有点像烧制前的泥坯修改。”郭静看着拖把划过的痕迹,“每一次修改都是对前一版的覆盖,但又留下隐约的痕迹。”
赵环点头,他想起自己电脑里那些层层叠叠的设计版本,最新的图纸下永远藏着最初的构想。就像地面的水痕,即使被拖去,也在地板的木纹里留下了短暂的湿润记忆。
离开咖啡馆时,阳光已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狂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叛逆小子)的经典小说:《狂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338220字07-05
- 我转生成兔子这档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树和小草)的经典小说:《我转生成兔子这档事》最新章节全...
- 555253字07-06
- 回到过去当歌神
- 回到过去当歌神章节目录,提供回到过去当歌神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437092字07-06
- 后宫佳丽三千我摆烂怎么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苏之酒)的经典小说:《后宫佳丽三千我摆烂怎么了》最新章节...
- 567640字10-31
- 官场,女局长助我平步青云
- 官场,女局长助我平步青云是由作者风中的阳光著,免费提供官场,女局长助我平步青云最...
- 2891046字05-28
- 今天也要努力攻略副本
- 2948754字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