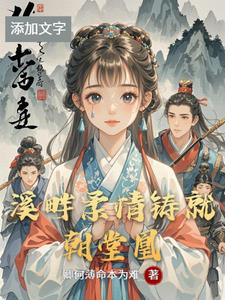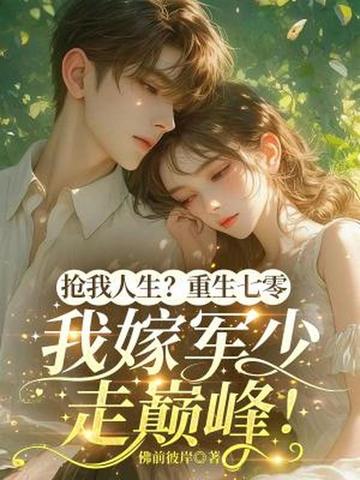第92章 陶土的记忆复苏
驳的光影,外婆的银发上沾着草屑,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里都落着光。
“外婆,为什么这泥比别的软?”她记得自己当时问。外婆把泥放在她手心里,轻轻合上她的手指:“因为这里头有老窑的火性,还有……”外婆顿了顿,用沾着泥的手指点了点她的胸口,“还有揉泥人的心气。”
现在想来,外婆说的“心气”,或许就是陶土里留存的生命痕迹。郭静将那团带釉料的泥捧到鼻尖,努力分辨着是否有窑火的味道,却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皂角香——那是外婆惯用的洗衣皂味道,每次揉完泥,外婆都会用皂角水洗手,指缝里总留着淡淡的清香。
她忽然想起有次外婆烧窑失败,一窑的茶盏都裂了纹。外婆蹲在窑门口,用指尖轻轻抚摸那些裂纹,半天没说话。她以为外婆会难过,没想到外婆忽然笑了:“你看这纹路,像不像后山的溪流?”说着就捡起一片碎瓷,在上面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缺陷不是毛病,是泥料在告诉你,它有自己的想法。”
郭静把碎陶片和带釉料的泥团放在工作台上,重新将手伸进麻袋。这一次,她不再是寻找什么,而是任由手掌在泥料里穿梭。泥料从指缝间滑落的触感,像极了外婆当年给她梳头发的力道,不轻不重,带着一种安抚的韵律。她闭上眼睛,想象着外婆当年揉这袋泥的场景——或许是某个冬夜,窑炉里的火正旺,外婆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揉泥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泥料在她掌下渐渐变得柔润,吸收着她手心的温度和呼吸的频率。
“陶土会记住经手者的体温变化。”郭静喃喃自语,想起自己在笔记里写过的话。此刻她掌心的温度正在传递给这袋老泥,而泥料里封存的外婆的体温,也在透过皮肤渗入她的血液。这种双向的温度传导,像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她忽然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执着于在作品中保留指纹和泥痕——那不仅仅是创作痕迹,更是手与陶土之间的契约,是生命与生命的共振。
她睁开眼,发现台灯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尘埃,在泥料上方形成一圈朦胧的雾。当她的手指再次触到麻袋底部时,摸到一个硬硬的角状物。掏出来一看,竟是个用泥捏成的小陶罐,只有拇指大小,罐口歪歪扭扭,显然是初学者的手艺。郭静的心猛地一缩,这是她八岁时捏的第一个陶罐,当时觉得太丑就扔了,没想到外婆一直收在泥料袋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小陶罐的底部还留着她当年刻下的歪歪扭扭的“静”字,笔画间塞满了干硬的泥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杀敌爆装:淞沪杀穿鬼子司令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嵩云文化)的经典小说:《杀敌爆装:淞沪杀穿鬼子司令部》最...
- 866901字07-12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溪畔柔情铸就朝堂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卿何薄命本为难)的经典小说:《溪畔柔情铸就朝堂凰》最新章...
- 421608字07-12
- 抢我人生?重生七零,我嫁军少走巅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佛前彼岸)的经典小说:《抢我人生?重生七零,我嫁军少走巅峰...
- 347488字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