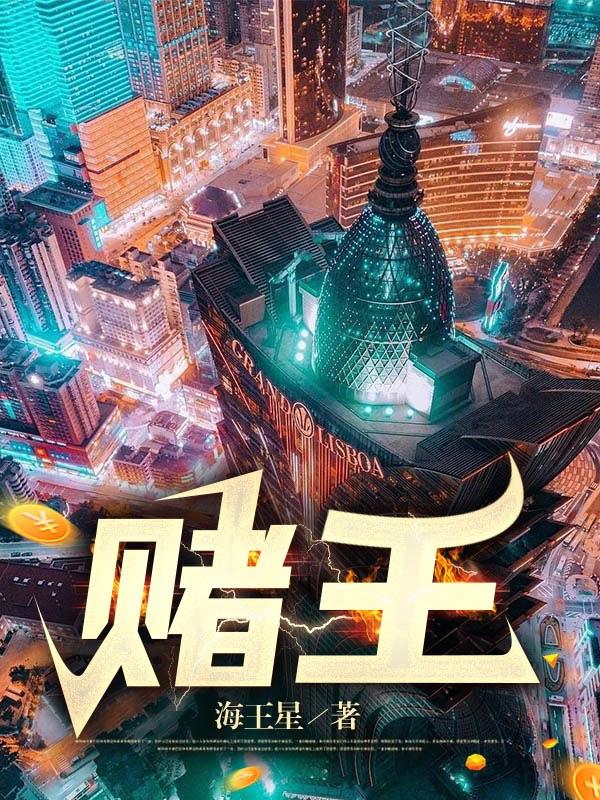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18章 陶轮转速的冥想时刻
窑炉里未烧的坯体都在轻轻共鸣。她想起《考工记》里“审曲面势”的句子,忽然意识到:陶土不是死物,它在等待某个频率,等待与匠人呼吸同频的瞬间。
三个月后,老师傅病倒了,窑炉不得不停火。郭静守在空荡的作坊里,对着转速表发呆。表盘上的红色指针像根断了的弦,停在115的位置。她鬼使神差地蒙上眼睛,凭记忆踩动踏板,直到耳朵捕捉到某种熟悉的嗡鸣——不是陶轮的噪音,而是更深沉、更规律的震动,像大地的心跳。
当她摘下眼罩,发现转速表正好停在120。泥坯在轮盘上静静旋转,表面没有任何外力塑形的痕迹,却自然形成了一个符合黄金分割的弧度。她想起外婆说过的“陶土会认手”,此刻才明白,那不是玄学,而是两种生命频率的相遇。
秋天来时,老师傅把一本油布包着的笔记塞给她:“里面有几页提到‘轮转速’,你……琢磨琢磨。”泛黄的纸页上,用朱砂画着古怪的图表,其中一张标注着“子午卯酉时,轮速百二十,土性乃活”。郭静的指尖划过墨迹,忽然想起三个月前那个梅雨天,当转速与心跳同频时,泥坯表面渗出的那层薄水——不是汗水,而是陶土本身的“呼吸”。
她开始做更疯狂的实验。在满月夜测转速,发现120转时釉料流动会呈现星芒状;在冬至日揉泥,120转的离心力能让泥团里的气泡排成北斗七星的形状。有次工作室停电,她靠脚踩维持转速,竟在黑暗中“摸”出了最完美的器型——后来才知道,那时她的心跳因为紧张飙升到了120次/分。
“搞这些虚的有什么用?”母亲在电话里骂她,“上次市集那批茶杯,口沿歪了三个,又被压了价!”郭静捏着听筒,看着窗外的月亮,忽然想起某个转速实验的夜晚:当轮盘转到120,月光透过天窗落在泥坯上,形成的光斑恰好是个完美的圆,而她的心跳,也在那一刻漏了一拍。
转折发生在次年春天。一个研究声纹的博士偶然参观她的工作室,对那台老陶轮产生了兴趣。当郭静演示120转/分的“冥想转速”时,博士突然指着示波器尖叫:“看!这是α波频率!和人脑放松时的脑电波一致!”屏幕上,陶轮震动的波形与郭静指尖的脉搏图,重叠成一朵奇异的花。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那天晚上,郭静在笔记里写下:“陶土在跳生命之舞,而我的手,是它的舞伴。”她想起老师傅说的“手的呼吸”,想起父亲账本上精确到分的釉料钱,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翻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有半毛钱关系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没得事)的经典小说:《有半毛钱关系吗?》最新章节全文...
- 567159字07-24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
- 甄嬛传:从替大胖橘做绝育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静语忘峰)的经典小说:《甄嬛传:从替大胖橘做绝育开始!》...
- 1632074字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