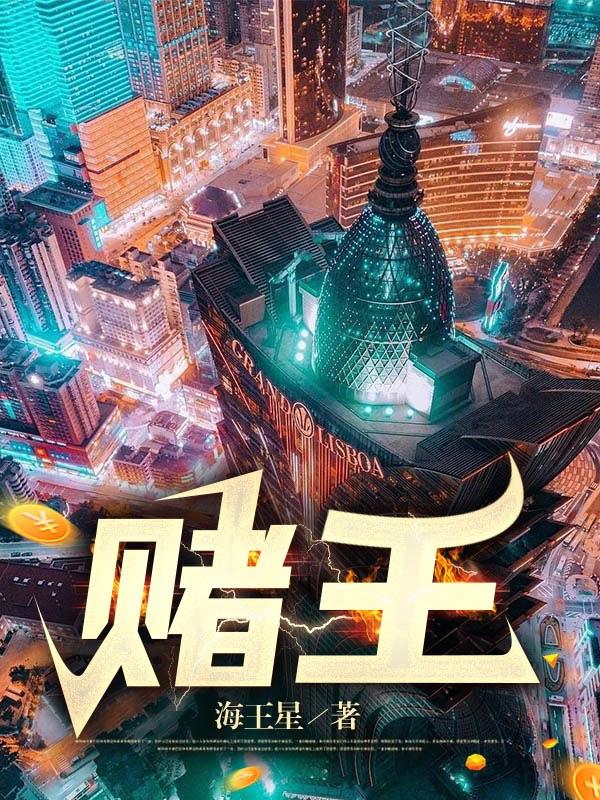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8章 窑炉笔记:手的呼吸论
的体温能让它升温0.3℃。”
李师傅用竹刀敲了敲她的手背:“数据是死的,手是活的。”他示范修坯,刀锋掠过坯体的声响像春蚕啃叶,“民国三十年大旱,我师父用干裂的手揉泥,烧出的茶盏全带冰裂纹,倒茶时会听见细碎的响,像雪落在竹叶上。”郭静盯着他布满老茧的拇指——那道深可见骨的疤痕,据说是某年窑变时为抢救坯体留下的,如今疤痕处的皮肤比别处厚上三分,摸泥料时却比秤更准。
梅雨停的那天,郭静在匣钵堆里找到半块残片。釉面下隐约有金色斑点,排列成不规则的星图。她想起七岁那年,外婆窑里炸裂的陶碗,火星溅在青石板上的形状,竟与这残片上的金斑分毫不差。“这是窑宝,”李师傅用指甲刮下一点釉屑,“当年有个英国商人出高价买带星斑的瓷,我师父偏要把它们砸了,说‘星星是天的,不该被锁在碗里’。”
深夜的工作室里,郭静把信笺铺在陶轮上。纸页吸收了空气中的潮气,边角微微卷起,像要飞走的蝴蝶。她忽然想起母亲总说“陶土是换米的”,可此刻指尖的泥料正顺着纹路爬升,在台灯下泛着珍珠母的光泽,像某种有生命的流体。当第一百次揉泥时,她发现掌心的螺旋状疤痕(三年前陶轮失控留下的)正与泥团的纹理形成共振,每按压一次,泥料里就渗出极细的气泡,在灯光下碎成星芒。
“手得先学会呼吸,”李师傅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手里端着一碗釉料,“这是我师父传下的‘星夜蓝’,钴料要掺三分老泥,念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入窑。”郭静接过釉碗,发现碗底刻着细小的星图,与她昨晚在笔记本上画的“星子坠入春水”如出一辙。
入秋时,郭静完成了第一件让李师傅沉默的作品。那是个粗陶水盂,表面保留着拉坯时的指纹,釉色在窑变后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像被搅碎的夜空。最奇特的是盂口的一道冰裂纹,从侧面看竟似北斗七星的勺柄。“你把‘手呼吸’悟到了,”李师傅用竹刀轻叩盂身,发出清越的响,“但记住,真正的好陶,要让泥土忘了自己是泥土。”
冬至前夜,郭静在窑炉前守夜。松木柴烧到最旺时,她把信笺凑到火边——纸页上的墨迹遇热竟浮现出淡金色的星轨,与笔记本里某页手绘的窑炉升温曲线重合。她忽然明白,所谓“手的呼吸”,原是让陶土记住每一次触碰的温度,就像老建筑的梁柱里藏着百年的风声。
离开景德镇那天,郭静把信笺和笔记本封进陶瓮,埋在龙窑的根基下。瓮身上刻着李师傅教的咒语:“土本无魂,因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有半毛钱关系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没得事)的经典小说:《有半毛钱关系吗?》最新章节全文...
- 567159字07-24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
- 姑奶奶的军婚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无解)的经典小说:《姑奶奶的军婚》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858716字07-20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