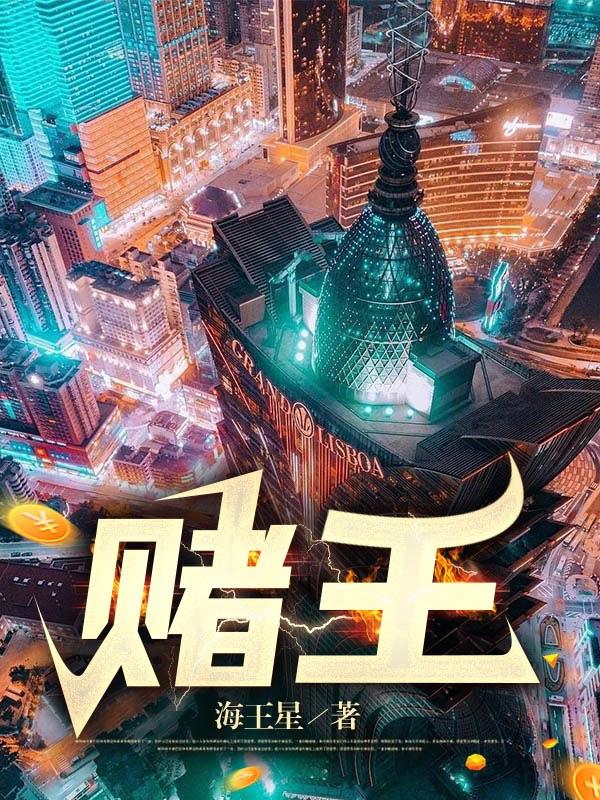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6章 掌心的永久细纹
梅雨季来了,空气湿得能拧出水,伤口总在半夜痒得厉害。郭静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打着手电筒看掌心的绷带,纱布缝隙里渗出的淡红色液体,在月光下像极了窑变时的铜红釉。她想起出事那天甩出的泥坯,断裂面呈现出奇异的螺旋纹路,老师傅说那是“土龙转身时留下的痕迹”。
拆绷带的那天,阳光很好。郭静对着窗户摊开手掌,一道浅粉色的疤痕盘踞在掌心,形状像极了陶轮旋转时甩出的弧线。她试着握拳,疤痕处的皮肤会轻微收紧,像有根无形的线牵着,让她想起拉坯时泥料在指间的阻力。“这纹路倒少见。”老师傅凑过来看,烟袋锅子差点烫到她的手,“像个小漩涡,往后捏坯时,这地方得使巧劲。”
秋天来临时,郭静第一次带着疤痕拉坯。陶轮转动的嗡嗡声里,她能清晰地感觉到疤痕处的皮肤与陶土摩擦的触感——那是一种比其他部位更敏锐的知觉,仿佛伤口愈合时新生的神经末梢,都化作了感知泥土的触角。当转速调到120转时,疤痕处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震颤,与陶轮的频率奇妙地重合,让她想起外婆窑炉里炸裂的陶碗,那些火星坠落时的微响。
“你这疤,倒成了泥性的指南针。”老师傅看着她拉出的坯体,弧度比以往更流畅,“有些泥料性子倔,得用带疤的手去摸,它才服帖。”郭静没说话,只是把掌心贴在泥坯上,能感觉到疤痕的纹路正与陶土表面的肌理形成某种咬合,像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她忽然明白,那次事故不是意外,而是陶土给她的成年礼——用一道永久的印记,让她记住人与泥土之间该有的敬畏与默契。
寒冬腊月,郭静在工作室整理碎陶片。一块窑变失败的残片边缘特别锋利,她不小心划破了手指,血珠滴在疤痕上,瞬间渗进那道螺旋状的浅纹里。她盯着掌心看了很久,忽然想起在景德镇陶瓷馆看到的宋代瓷片,上面也有类似的螺旋纹,解说词说是“工匠捏坯时的无意识痕迹”。可她知道,那不是无意识,那是手与陶土对话时,留下的独特声纹。
开春后,老师傅让她尝试做一批“星夜”系列的花瓶。郭静调配釉料时,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直到某天夜里,她梦见自己的疤痕在发光,像指南针一样指向窑炉的方向。醒来后,她鬼使神差地取了点指尖血,混进钴料里——这是老师傅绝对禁止的“邪门歪道”。出窑那天,当她擦去瓶身的窑灰时,突然愣住了:蓝色的釉面上,金色的斑点分布竟与疤痕的螺旋轨迹完全一致,像星子坠入春水时荡开的涟漪。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有半毛钱关系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没得事)的经典小说:《有半毛钱关系吗?》最新章节全文...
- 567159字07-24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
- 姑奶奶的军婚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无解)的经典小说:《姑奶奶的军婚》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858716字07-20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