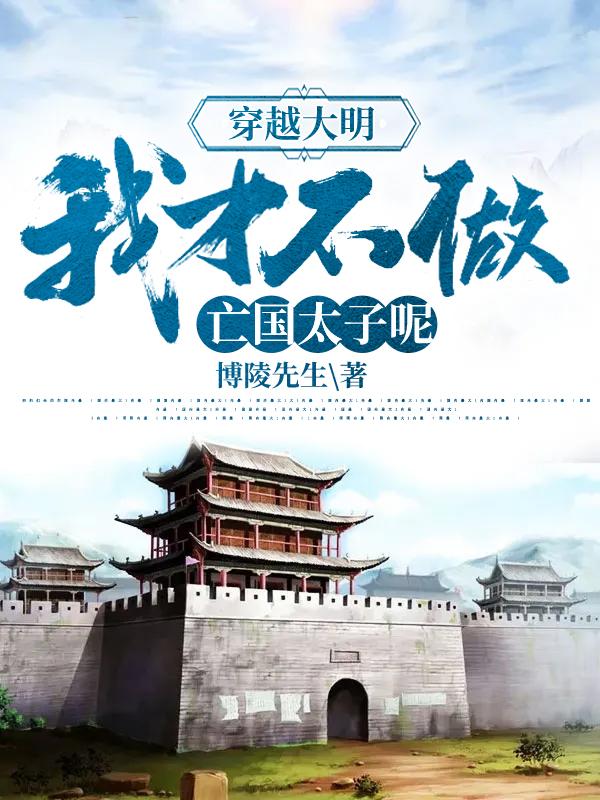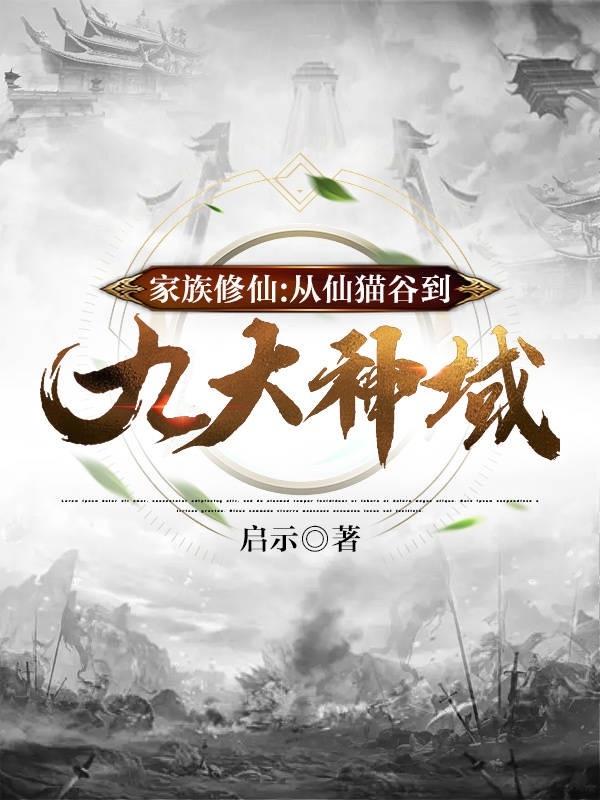第147章 春诏均田
平城的春雪来得迟,三月初二的太极殿外还堆着残雪,檐角的冰锥滴着水,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的响。陈五站在丹墀下,玄色朝服的广袖沾了晨露,腰间的鱼符硌着胯骨 —— 这是拓跋濬登基后新赐的 "安边鱼符",玄鸟纹用金线绣在银胎上,比从前的更沉些。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司礼太监的尖嗓子在殿内回荡。陈五望着龙案后的少年皇帝,拓跋濬的剑穗在案角晃着,胡汉两色的丝线被炭火烤得暖融融的。他想起半月前在太庙,少年捧着太武帝的牌位说 "朕要把爷爷的均田令再铺开" 时,眼里的光和甜市屯田点的麦芒一个亮。
"臣拓跋拔有本启奏。" 西首的鲜卑老臣跨前一步,皮裘上的狼头银扣撞出脆响。他是太武帝时期的镇北将军,此刻白眉倒竖,"新帝初立,当以稳国本为先。太武帝的均田令推行时,鲜卑贵族丢了千顷牧场,汉人豪强失了万亩良田,如今旧事重提,恐生乱!"
陈五的手指在鱼符上摩挲。他想起甜市屯田点的胡汉百姓,想起阿史那云的狼骑和李昭的玄甲卫在田埂上分麦饼的模样,喉结动了动:"拓跋大人,甜市推行均田三年,胡汉百姓共垦荒五千顷,去年秋粮比往年多收三成。牧民把草场分一半给汉农种苜蓿,汉农教牧民修水渠,哪家不是粮仓满、马膘肥?"
"甜市是边镇特例!" 拓跋拔拍了拍腰间的玉板,"平城周围的贵族庄园,哪家没养着三百私兵?动他们的地,就是动他们的命!" 他转向龙案,"陛下,当年太武帝推行均田,被刺客砍了车驾;文成帝想接着办,被老臣们拦在承明殿外哭了三日 —— 这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殿内突然安静下来。陈五听见身后的汉臣崔浩咳嗽了一声,想起昨夜在崔府,老臣摸着《均田疏》说 "当年太武帝的朱批还在,可人心变了" 时的叹息。他摸出袖中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卷,是甜市百姓按的血手印:"陛下,这是甜市八百户百姓的联名信,说 ' 均田令是甜饼,谁都能咬一口 '。" 他展开纸卷,血印在晨光里像片红莓,"去年冬天,甜市的鲜卑老妇把陪嫁的银镯子捐出来买耕牛,汉家小子把祖传的犁铧分给牧民 —— 这不是乱,是人心聚了。"
拓跋濬的手指在御案上敲了敲,剑穗扫过案头的《魏书》。陈五看见他的目光落在 "太武纪" 那页,那里夹着片干苜蓿叶,是甜市牧民送的:"拓跋大人,朕记得您在漠南打柔然时,说过 ' 兵无粮草,不如弃甲 '。均田令就是给大魏的兵囤粮草,给百姓的胃填甜饼。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956967字07-27
- 穿越大明:我才不做亡国太子呢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博陵先生)的经典小说:《穿越大明:我才不做亡国太子呢》最...
- 4035623字09-10
- 秘境制造者,幕后赚麻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雪中银龙)的经典小说:《秘境制造者,幕后赚麻了》最新章节全...
- 608854字09-10
- 巫界征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北辰之影)的经典小说:《巫界征途》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8565380字07-29
- 家族修仙:从仙猫谷到九大神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启示)的经典小说:《家族修仙:从仙猫谷到九大神域》最新章...
- 4321914字07-29
- 洪荒之万界主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墨韵2024)的经典小说:《洪荒之万界主宰》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253397字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