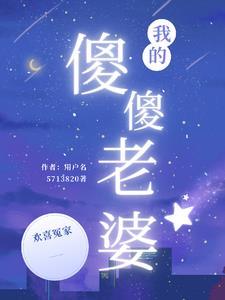第6章 冷库的真相
晚风像一把钝刀,割过脸颊,将我兜帽吹得向后翻去。
老吴在图纸上用红圈标注的“母亲”二字,像炭火般烙在我的视网膜上。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翻涌,摸出那把从王建国办公室“借”来的万能钥匙。
冰冷的金属触感从指尖传来,如同三年前陈野牺牲时,我从他胸口扯下那半枚警徽的瞬间。
B4区尽头的应急通道铁门锈迹斑斑,门轴发出垂死的呻吟。
德国进口的锁芯在王建国的特制钥匙下,只轻微抵抗了一下,便“咔哒”一声弹开。
一股混合着霉味与制冷剂的寒气扑面而来,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
我侧身闪入,身后铁门自动合拢的闷响在空旷的通道内回荡。
帆布包里的温差仪外壳冰冷,我取出它,按下启动键,幽蓝的屏幕亮起,数字在-18℃和-19℃之间跳动。
这里是冷库的外围缓冲区,温度不算极端。
按照图纸的指引,我穿过一排排高耸的货架,上面堆满了标记着各种生鲜食品的白色泡沫箱。
空气越来越冷,呼吸间已能看到清晰的白雾。
温差仪上的数字持续下降,很快便稳定在了-22℃。
这里应该是冷库的核心区域。
我开始仔细扫描,温差仪的探头掠过每一寸金属壁板。
突然,屏幕上的数字在一块特定的区域微微跳动了一下,从-22.1℃瞬间升至-21.8℃,然后又迅速回落。
细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波动,却像一根针刺入我的神经。
我蹲下身,仔细观察那块壁板。
金属表面覆盖着一层均匀的薄霜,但在某个角落,霜花的形态似乎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
我从包里取出一支高倍放大镜,凑近观察。
普通情况下,-22℃恒温形成的冰晶应该是细密而规整的针状结构。
但这里的冰晶,边缘略显圆融,晶体间隙也较大,更像是经历过一个相对“温暖”的阶段后再次快速降温形成的。
“有人动过这里的温度。”我喃喃自语。
大脑飞速运转,调取着关于冷凝水结晶的数据库。
如果这里曾被设定在-18℃左右,持续一段时间,再迅速降至-22℃,就能形成这种不规则的晶体形态。
-18℃……这个温度,恰好是许多特殊生物制剂,或者说,离体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我转生成兔子这档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树和小草)的经典小说:《我转生成兔子这档事》最新章节全...
- 555253字07-06
- 寸止( sp 强制)
- 寸止( sp 强制)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寸止( sp 强制)》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
- 259223字09-28
- 官场,女局长助我平步青云
- 官场,女局长助我平步青云是由作者风中的阳光著,免费提供官场,女局长助我平步青云最...
- 2891046字05-28
- 峰宇之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用户名5713820)的经典小说:《峰宇之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478799字11-24
- 狂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叛逆小子)的经典小说:《狂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338220字07-05
- 赤之沙尘
- 赤之沙尘章节目录,提供赤之沙尘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45574字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