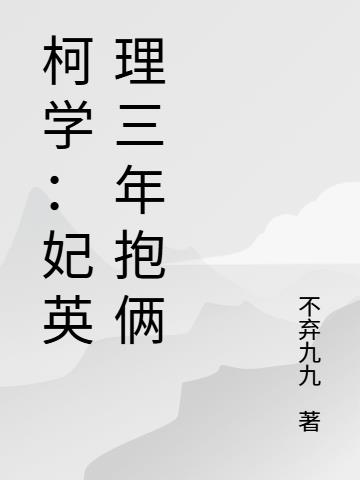第161章 孝子泉
青牛村的蝉鸣裹着暑气,把个夏天烤得冒油。村东头草棚里,王阿婆咳得床板直晃,枯瘦的手攥着儿子阿顺的衣袖:"顺儿,娘这心口像压着块磨盘,怕是要见阎王喽......"
阿顺跪在草席上,额头抵着母亲的手背。他知道娘得的不是寻常病——半月前上山采野果,被野蜂撞进刺丛,腿上划了道血口子,本是小伤,偏巧伤口发了紫,接着就咳血、发烧。村里最年长的陈郎中捻着白胡子直叹气:"这是寒毒入肺,需得鹰嘴崖上的冰蝉草才能救。可那崖壁陡得能刮掉人一层皮,崖顶还住着吃人的山魈......"
"娘,我明儿就去。"阿顺把母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冰蝉草再难采,我也给您摘回来。"
第二日鸡叫头遍,阿顺就往鹰嘴崖去了。他腰里别着柴刀,肩上挂着水囊,脚底板绑了层粗布——陈郎中说,冰蝉草喜阴,得赶在露水未干时采摘。可刚爬到半山腰,日头就毒得人睁不开眼。阿顺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水囊早空了,喉咙里像塞了团烧红的炭。
"阿顺——"
山风里飘来一声唤,阿顺抬头,见山路上歪歪扭扭躺着个讨饭的老头,灰布褂子破得像鱼网,脚腕子上血肉模糊。"小哥,行行好......"老头伸出手,指甲缝里全是泥。
阿顺摸出怀里的半块炊饼,蹲下来递过去。老头却没接,盯着他的水囊笑:"你这水囊倒是满的,怎的不喝?"阿顺一愣——水囊早空了,许是方才滚下斜坡时漏了。他尴尬地挠头:"许是我记错了。"
老头突然抓住他的手腕,指甲几乎掐进肉里:"你这娃,心善是好,可这鹰嘴崖的冰蝉草,不是凡人能采的。"阿顺急了:"我娘快不行了,再难我也得去!"
老头松开手,指了指山顶:"去吧,记着,到了崖顶,见着三棵合抱的马尾松,往松树下跪。"说完便往林子里钻,眨眼没了影。
阿顺爬到崖顶时,太阳正毒。三棵马尾松像三把绿伞立在崖边,树下有块青石板,石板上凝着层水珠。他扑通跪下,膝盖磕在石头上生疼,可这点疼算什么?他想起娘咳血时染红的帕子,想起冬夜里娘把唯一的棉被盖在他身上,想起自己发疹子时娘整宿守着用草药敷......
"咚、咚、咚",额头磕在青石板上,渗出血珠。阿顺哑着嗓子喊:"山神爷,求您显显灵!我娘病得快不行了,只要能采到冰蝉草,我愿用这条命换!"
话音刚落,石板下传来"叮咚"一声响,像有人敲玉盘。阿顺抬头,见石板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2页
相关小说
- 灵异万界
- 灵异万界是由作者6拽著,免费提供灵异万界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线阅读。
- 1401970字04-28
- 天棺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螺丝汤)的经典小说:《天棺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162514字06-29
- 网游之复活
- 753393字07-03
- 光头武僧在都市
- 972450字07-03
- 柯学:妃英理三年抱俩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不弃九九)的经典小说:《柯学:妃英理三年抱俩》最新章节全...
- 802837字07-04
- 诡异游戏?这不是恋爱游戏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咸鱼的咸鱼生活)的经典小说:《诡异游戏?这不是恋爱游戏吗...
- 476804字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