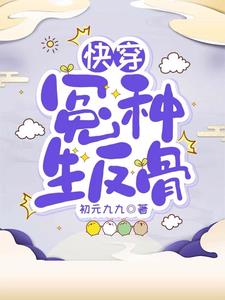第177章 平遥牛肉的「盐与时间九月初四」
清代传到现在,每年添新肉不换汤,跟咱平遥古城似的,越老越有滋味。」
??李可佳蹲在灶台前,看卤汤从「咕嘟」冒小泡,到「翻涌」成浪花——牛肉在汤里沉浮,表面的盐粒渐渐融化,肉色从浅红变成深褐,「卤煮得『三起三落』,大火煮透、小火焖香、关火浸味,总共八小时,让卤香渗进肉纹的每个缝。」
??骆梓淇拍下她的睫毛——蒸汽凝成的水珠挂在睫尖,背景里的老灶台砖缝渗着卤油,像幅「会呼吸的古画」。画外音是卤汤的「咕嘟」声、木勺刮擦锅底的「吱呀」响,还有王师傅的念叨:「当年走西口的商队,揣着咱的牛肉干,在戈壁滩上啃一口,咸香能顶半天饥,这肉里啊,藏着古驿道的风。」
四、作坊漫走:从盐粒到肉香的「驿道密码」
??正午的阳光穿过作坊木窗,在卤锅上投下菱形光影。李可佳跟着王师傅逛「牛肉博物馆」:玻璃展柜里,清代的「牛肉税票」、民国的「镖师带肉腰囊」、现代的「非遗证书」依次排列,最显眼的是张老照片——1930年代的平遥街头,货郎挑着扁担,筐里的牛肉用荷叶包裹,插着「地道平遥」的小旗。
??路过「古驿道复原区」时,看见匠人正在模拟「牛肉风干」:牛肉条挂在麻绳上,穿堂风掠过,带走最后一丝水汽,「以前商队赶路,就这么让风把肉吹干,盐粒锁住水分,能存三个月不坏,跟咱平遥商人『精打细算』的劲儿一个道理。」
??坐在「牛肉雕塑」前的石阶上,李可佳忽然懂了:平遥牛肉的「咸香」,原是古驿道的「风尘」——盐粒是路上的「守护者」,时间是途中的「雕刻家」,就像王师傅说的「一块牛肉要『过三关』:盐关、卤关、风干关,缺一不可,跟咱晋商走西口过的『杀虎口、张家口』一样,都是『闯出来的滋味』」。
五、暮色中的「牛肉顿悟」:从「盐粒」到「肉纹」的「时光沉淀」
??傍晚六点,卤锅的火渐渐熄灭,王师傅用铁钩捞出牛肉——深褐色的肉块冒着热气,用手轻轻一撕,肉丝呈「放射状」散开,肉纹里渗着浅红色的卤汁,「趁热吃,尝个『刚出锅的鲜』。」
??李可佳捏起一条牛肉——肉质紧实却不柴,盐的咸香混着卤的醇厚,在舌尖炸开,尾调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焦香,「这肉纹看着像古驿道的车辙印,一圈圈的,全是时间压出来的。」骆梓淇拍下她撕肉的瞬间:肉丝在指尖断开,卤汁滴在青石板上,背景里的老城墙在暮色中泛着暖光,「你看这肉丝,每一根都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
- 快穿:冤种生反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初元九九)的经典小说:《快穿:冤种生反骨》最新章节全文阅...
- 1343306字04-02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时间裂缝:我想回家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红色的稻穗)的经典小说:《时间裂缝:我想回家》最新章节全...
- 747393字07-01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