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碑影寺异闻录
乾隆五十二年秋,我因访友行至保定府清苑县地界。时值暮雨潇潇,道路泥泞如泥。天色向晚,四野苍茫,唯见道旁山坳处隐隐透出一点昏黄灯火。拨开半人高的乱草寻去,竟见一座古寺破败山门,匾额斜挂,字迹漫漶难辨,只余“碑影”二字尚可揣摩。门内荒草侵阶,断碑仆地,唯西厢一室窗纸透出豆大光亮。
轻叩柴扉,吱呀一声自行开启。室内仅一榻、一桌、一灯如豆,有位枯瘦老僧盘坐蒲团,眼皮低垂,似睡非睡。
“雨夜迷途,求借宝刹一席之地避雨。”我拱手道。
老僧眼皮未抬,只伸枯指点了点墙角一捆稻草。我依言铺开草席,解下湿透外袍。窗外风声呜咽,雨打残瓦,其声如泣。正欲解衣就寝,忽闻老僧喉间发出枯木摩擦般的声音:
“施主且慢睡。”
我悚然一惊,但见老僧已睁开双眼,眸中精光湛然,竟无半分浑浊:“此寺名‘碑影’,非为虚言。子时将近,有物将出。”
话音未落,窗外骤然风狂雨骤,豆大灯焰剧烈摇曳,将老僧嶙峋身影投在斑驳土墙上,形如张牙舞爪的山魈。他枯指忽地指向窗外院落:“看那断碑。”
一道惨白电光裂空而下,瞬间照亮庭院。但见风雨中,半截残碑竟如浸水宣纸般渐渐透明,碑后缓缓浮出一个朦胧人影——青衫方巾,书生打扮,身形僵直如提线木偶,唯颈间一道深紫勒痕触目惊心。
“此乃成化年间落第秀才柳文渊,”老僧声音幽沉,“因科场舞弊案牵连,悬梁于此。怨气凝结,每逢雨夜便现形。然其所执迷者,非冤屈本身……”
狂风卷着雨沫扑入破窗,灯火明灭间,墙上书生鬼影的脖颈竟诡异地扭转向内室,空洞眼窝直勾勾“盯”住墙角——那里唯有一尊蒙尘的陶土香炉。
老僧从怀中摸出三枚乌黑油亮的核桃,摩挲着道:“当年柳生赴考前,其母在佛前许下大愿:若儿得中,必重塑金身,捐百斤灯油。后虽蒙冤自尽,老母仍日日来此焚香祷告,直至哭瞎双目而亡。”他将核桃轻轻置于香炉前,“此乃柳母所遗,浸透慈母泪。”
子时钟声自遥远村落传来,混在风雨中几不可闻。炉前核桃忽地微微颤动,竟自行裂开细缝。香炉内积年香灰无风自动,簌簌聚成三缕轻烟,如灵蛇般钻入核桃缝隙。墙上鬼影颈间勒痕竟随之变淡,僵直身躯渐趋柔软。
“看那香炉底。”老僧低语。
我凑近细观,烟熏火燎的炉底隐约可见数行刻痕:“信女周氏,愿减寿十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灵异万界
- 灵异万界是由作者6拽著,免费提供灵异万界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线阅读。
- 1523120字07-15
- 与婆婆同居的日子
- 与婆婆同居的日子章节目录,提供与婆婆同居的日子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32048字06-16
- 地府临时工
- 4008351字06-17
- 炮灰求生,但ABO世界[gb]
- 炮灰求生,但ABO世界[gb]章节目录,提供炮灰求生,但ABO世界[gb]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766960字07-17
- 被国足封杀后,在西甲肝属性成球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国足何时进世界)的经典小说:《被国足封杀后,在西甲肝属性成...
- 1327748字06-23
- 【mob】饮月君的淫荡生活
- 21540字06-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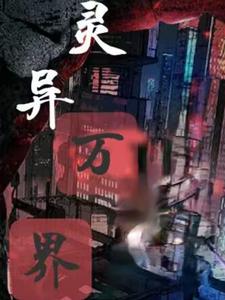


![炮灰求生,但ABO世界[gb]](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1/61850/61850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