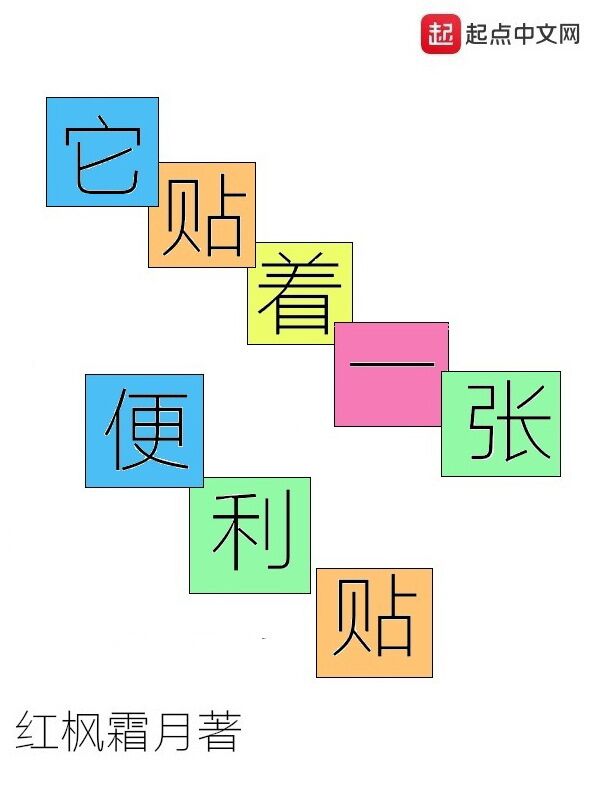第168章
漠北前线的风刚捎来算学军医培训结业的消息,第七日头上,河西牧场的日头就把地皮晒得发烫。刘妧撩开草窖口的粗麻布帘时,指尖先触到了里头透出来的阴凉气——这是用夯土混合了炭屑砌成的窖壁,入夏时特意让人在四壁糊了层新割的芦苇,如今掀开,里头那股子酸甜带草腥的味儿直往人鼻子里钻。
“公主您瞧,”旁边蹲守的老牧民王老汉撩起一角草席,露出底下青碧色的苜蓿垛,“昨儿个刚封的窖,今个儿翻开来瞅瞅,愣是没见着一星黄霉。”他手里攥着根木扦子,戳进草垛里再拔出来,上头挂着的草丝儿还带着潮气,泛着股子像酸浆水似的清香。
刘妧蹲下身,指尖捻了捻那草丝儿。她记得前几日来看时,牧民们按老法子堆在敞篷里的牧草,这会儿早枯得跟柴火似的,叶边卷着黄,风一吹就往下掉碎屑。昨儿夜里她去看,那堆干草底下果然霉了大半,黑黢黢的一片,挨着的牧草都沾了灰扑扑的霉斑。
“王伯,前儿个让您称的那两捆草,分量差多少?”她问。
王老汉咧开嘴,露出颗缺了角的牙:“差老鼻子了!您那法子窖藏的,十斤干草能出八斤半好料,咱老法子堆的,十斤倒有五斤半烂在地里头!”他掰着手指头算,粗糙的指甲缝里还沾着草汁,“就昨儿个,我家那小子背了捆去马厩,咱那匹老骒马闻着味儿就直刨地,吃起来跟抢似的。”
正说着,外头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人扯着嗓子喊:“让开!让开!呼衍大人来了!”
刘妧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上的草屑。只见日头底下,一群牧民拥着个穿羊皮氅的汉子走来,那人腰间挂着根油光水滑的牧鞭,鞭梢系着撮狼毛,走起来一甩一甩的。他身后跟着的人手里举着兽皮幡,上头画着些看不懂的花纹,领头的几个还扛着杆狼头旗,旗子边角让风吹得噼啪响。
“刘公主,”那汉子开口,声音像磨砂似的,“我听说你在这草窖里搞名堂,把好好的牧草蒸煮发酵,囚禁在这土坑里?”他指了指草窖,“我匈奴牧人逐水草而居,草枯草荣都是天意,你这算学法子,莫不是要触怒草原母神?”
这人是休屠王部的牧民领袖呼衍朵,河西这带大半的牧草交易都经他的手。刘妧记得前几日查账本,军马场收的干草里,有六成是从他名下的胡杨牧场来的,可那些草看着金黄,实则掺了不少沙子,喂了没几日,好几匹马都开始掉膘。
她没接话,只朝旁边的小兵使了个眼色。那小兵抱来一捆干草,正是前日从呼衍朵牧场收来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求生:魔法灾变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水沧澜)的经典小说:《求生:魔法灾变世界》最新章节全文...
- 1323949字11-23
- 仙界穿越来的御兽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四月末的风)的经典小说:《仙界穿越来的御兽师》最新章节全...
- 287048字07-27
- 工具人都在觊觎我
- 工具人都在觊觎我章节目录,提供工具人都在觊觎我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62282字07-23
- 海平线的末日挣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心直口快的林锦)的经典小说:《海平线的末日挣扎》最新章节...
- 3740441字07-25
- 新星家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沈湖)的经典小说:《新星家园》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1044367字12-15
- 它贴着一张便利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红枫霜月)的经典小说:《它贴着一张便利贴》最新章节全文阅...
- 2635094字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