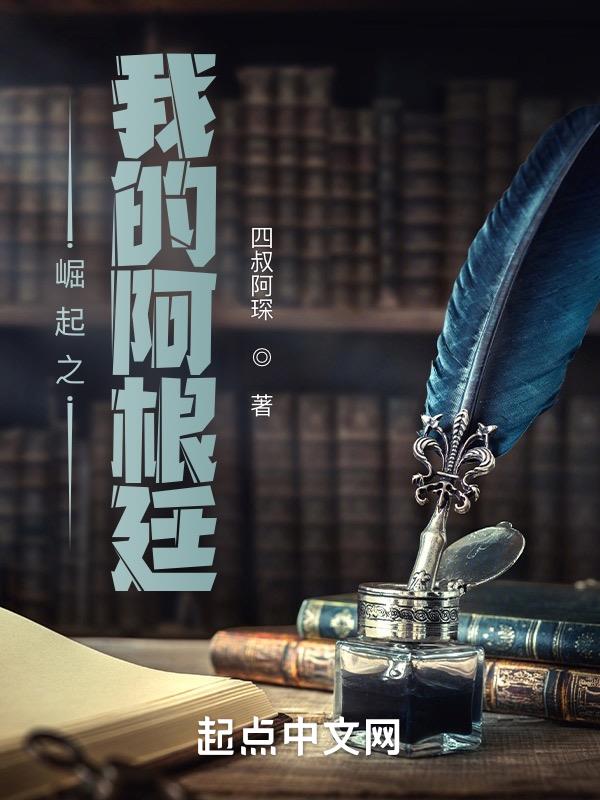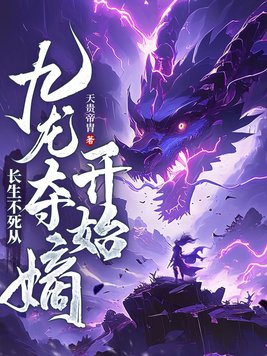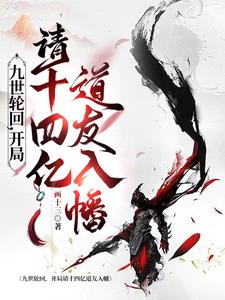第208章 血字舌根惊夜魄,孤臣何惧虎狼心
卷首语
《大吴会典?文书式》载:" 凡内外官署文移往来,皆须以火漆固封,钤缝印信。其印识各有定式:宗人府用双鹤纹,取仙禽守籍之意,彰宗室贵胄之尊;户部用嘉禾纹,绘五谷垂穗之形,寓仓廪充实之兆;巡抚衙门用獬豸纹,刻独角触邪之像,显风宪官执法之严。诸司文书,无印者视为伪书,印不符者以私启论处。
若有私启公文者,杖一百、徙三年;擅自改易印识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内外勾连、伪造印信者,凌迟处死,籍没全家。御史巡按承天子耳目之寄,持节所至,得开验官署封缄,辨印信之真伪,究勾连之奸宄。敢有阻挠者,罪同抗旨,从重论处。"
血字舌根惊夜魄,孤臣何惧虎狼心
永熙六年深秋,南昌城的夜风裹挟着鄱阳湖的潮气,如浸了冰的刀刃般割过谢渊的面。他隐在巡抚衙门后巷的阴影里,指尖反复摩挲着袖中玄夜卫腰牌,冰凉的金属质感让他愈发清醒 —— 三日前宗人府地窖的惊险遭遇,让他不得不对每一个细节都绷紧神经。更鼓初响,他避开正门的灯笼,贴着爬满青苔的墙根迂回而入,靴底碾过落叶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巡抚衙门后堂的烛火在穿堂风中摇曳,将师爷伏在案头的身影投在雕花屏风上,像极了一张扭曲的蛛网。谢渊踏入门槛时,故意将袖口掠过堆满田册的案角,余光扫见师爷青衫袖口翻卷处,那抹暗红的火漆印 —— 双鹤展翅的纹路,与宁王榷场的封条、惠民仓的粮册如出一辙。他的瞳孔倏地收紧,如利刃出鞘时的寒芒一闪而逝,喉间逸出一声极轻的气音,尾音几近消散在烛影摇曳的褶皱里。面上却眉梢微挑,唇角扬起半弧似笑非笑的弧度,袍袖拂过案头时指尖有意无意划过火漆印边缘:"贵衙的火漆印倒是格外精致,某在别处倒是少见。" 这抹笑意像蒙着薄冰的春水,底下暗涌着查案多年养成的审慎锋芒 —— 双鹤纹不该出现在巡抚衙门的文书上,就像豺狼披上了羔羊的皮毛,看似无害,却藏着噬人的尖牙。
师爷握笔的手顿在 "抗税" 二字上,墨汁在纸页上晕开一团污渍,如同滴在雪地上的血:"御史大人谬赞,不过是按例封存罢了。" 他抬头时,镜片后的目光略显躲闪,袖口的火漆印随抬手动作舒展,鹤首所指方向,竟与谢渊暗记在心中的宁王庄田分布图分毫不差。谢渊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中银针 —— 那年在魏王府,他正是用这银针挑开了匠人黄册的篡改痕迹,此刻,这银针似乎又在提醒他,眼前的田册,必定也藏着见不得人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占个山头当大王
- 5181029字06-26
- 快穿疯批恶女:赚功德养崽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依丽萍)的经典小说:《快穿疯批恶女:赚功德养崽崽》最新章...
- 253106字07-12
- 崛起之我的阿根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四叔阿琛)的经典小说:《崛起之我的阿根廷》最新章节全文阅...
- 661956字12-07
- 长生不死从九龙夺嫡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天贵帝胄)的经典小说:《长生不死从九龙夺嫡开始》最新章节...
- 1000441字12-03
- 九世轮回,开局请十四亿道友入幡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画十三)的经典小说:《九世轮回,开局请十四亿道友入幡》最新...
- 2231329字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