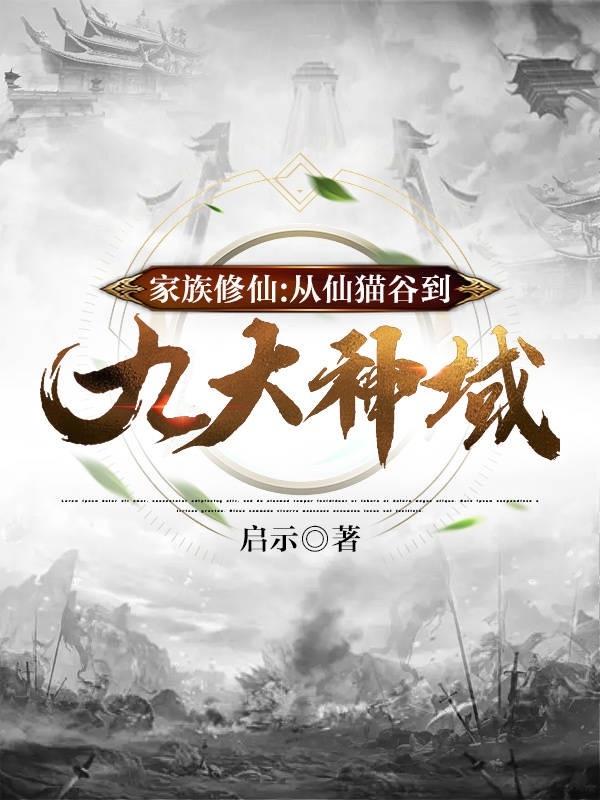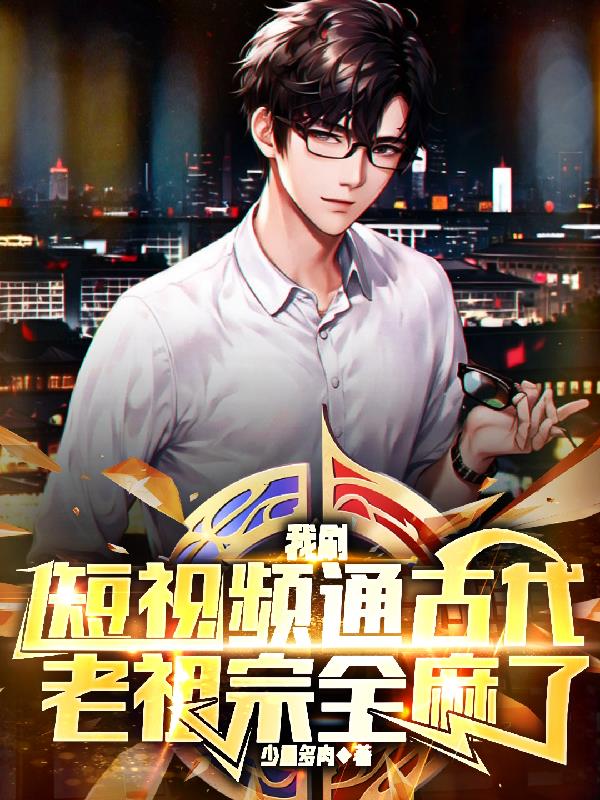第362章 广东十三行
代)着《西洋杂咏》,以七言诗记录英商生活(“红毛馆里宴嘉宾,烧猪烧鸭荐八珍”),既显文化修养,又暗合对外商的笼络。在商业交往中,行商以“义利之辨”自律——1803年,美国商船“富兰克林号”遇台风失事,货物漂至广州湾,十三行商人集体出资赎回,交还美国商人,分文未取,此事被美国报纸报道,成为“中国商人诚信”的例证。
与外商的“跨文化对话”充满智慧。语言不通,便创造“广州英语”(Cantonese Pidgin)——以英语词汇为基础,掺杂粤语、葡萄牙语语法,如“chop”(票证,源自粤语“戳”)、“cumshaw”(小费,源自粤语“多谢”),成为贸易通用语。文化差异,则用“虚拟亲属”化解:伍秉鉴与美国商人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结为“契爷契仔”(干爹干儿),福布斯获怡和行独家代理资格,后用利润投资美国铁路,成为波士顿巨富;英商渣甸(William Jardine)认行商卢文锦为“世伯”,通过宗族称谓规避官方交涉的繁琐。这种“文化折衷”既维护了帝国的“天朝上国”体面,又保障了商业效率。
四、生存体系:全球贸易网络的枢纽
十三行的生存根基,是其构建的“横跨陆海、连接东西”的贸易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是商品的流动,更是资本、技术、信息的交换,使广州成为18-19世纪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
商品贸易的“双向流动”重塑世界市场。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茶叶占比最大——1830年出口量达2.2万公吨,占欧洲消费量的80%,其中武夷红茶、西湖龙井、安徽祁门茶最受欢迎,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在广州设立“茶叶品鉴室”,雇佣中国茶师培训英商。生丝与土布紧随其后,1820年出口生丝1.5万担(每担60公斤),主要销往英国曼彻斯特、法国里昂的纺织厂;南京布(Nankeen,因产自南京周边得名)因耐用性成为美国西部牛仔的首选,1835年出口量达300万匹。进口商品则以白银为主(占70%),1750-1800年约有1.5亿银元流入中国,支撑了清帝国的货币体系;此外还有英国毛织品(因不适应中国市场,常亏损销售)、印度棉花(弥补中国棉花缺口)、钟表(供官僚收藏)、鸦片(19世纪后成为主要进口品,1838年达4万箱)。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十三行街”的商业集群效应显着。这条长约1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956967字07-27
- 家族修仙:从仙猫谷到九大神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启示)的经典小说:《家族修仙:从仙猫谷到九大神域》最新章...
- 4321914字07-29
- 洪荒之万界主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墨韵2024)的经典小说:《洪荒之万界主宰》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253397字11-21
- 我刷短视频通古代,老祖宗全麻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少面多肉)的经典小说:《我刷短视频通古代,老祖宗全麻了》最...
- 1539306字07-01
- 红人
- 红人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红人》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一本情节与文笔俱佳的...
- 960270字06-30
- 乱战三国之争霸召唤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霄落雪)的经典小说:《乱战三国之争霸召唤》最新章节全文...
- 6286289字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