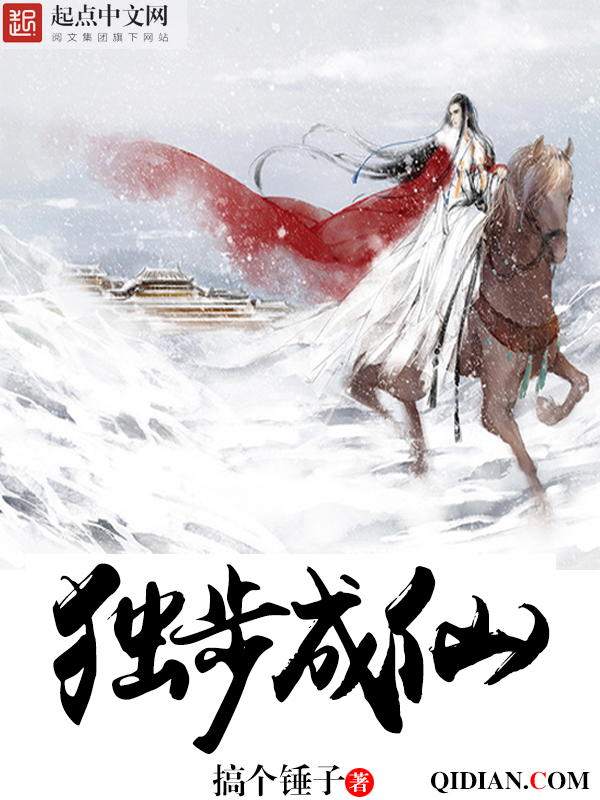第22章 有决心毅力攀登高峰
州”,每到贬所,必兴水利、办学堂、着书文,把“人间地狱”踏成“精神道场”。
他的毅力,藏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从容里——骤雨打湿衣襟,便把雨具让与僮仆;前路泥泞难行,便“竹杖芒鞋轻胜马”。就像泰山挑山工,肩负重物却走成“之”字路线,看似迂回,却在“一步一喘”中逼近山顶——真正的攀登者,从不怕“路长”,只怕“心怯”。
三、自然隐喻:山的褶皱里,藏着毅力的“生长法则”
(一)山脚:别问“山有多高”,先问“第一步落在哪里”
《道德经》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珠峰攀登者在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休整时,必先练“踩冰爪、结绳扣”的基本功,恰如明代地理学家罗洪先绘《广舆图》,先从“量算里距、考证道里”的细活做起。
山脚的意义,在于“把宏大目标拆成可触摸的当下”。徐霞客初登雁荡山,面对“壁立千仞”的大龙湫,先寻“枯藤为梯,足蹈手攀”的突破口;玄奘出长安时,未必预见十七年坎坷,却清楚“今日过一城,明日渡一河”的小目标——就像敦煌画工绘制经变画,先勾线条,再敷色彩,看似“局部劳作”,终成“满壁风动”的大观。
(二)陡坡:当“想放弃”时,问问自己“为何出发”
黄山“鲫鱼背”路段,宽仅尺许,两侧是万丈深渊,却见挑夫担着重物稳步前行——他们的眼里,不是脚下的险,而是山顶的“需求”。北宋科学家沈括晚年写《梦溪笔谈》,目力衰退仍“秉烛夜书,以指甲划字于纸”,只因记着“世间奇技淫巧,当有传焉”的初心。
陡坡是毅力的“试金石”,如《周易·坎卦》“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每一次跋涉,都是对“初心”的重认。徐霞客在云南腾越染病,“僵卧竹床,邻榻俱无”,却坚持记录“此地多火山,石色赤黑”;玄奘在恒河遇盗,被推至祭台,仍“正念观自在菩萨,愿得加被”——当“目标”具象成“山顶的光”,身体的疲惫便会退成背景音。
(三)山顶:真正的“登顶”,是看见“下一座山”
《徐霞客游记》终篇记“鸡足山志”,此时他已“两足俱废,不能复陟”,却命仆人“取纸墨,口授经义”——登顶不是终点,而是“看见更远处山”的新起点。就像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又遣班超“投笔从戎”,让“凿空”精神代代相传。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山顶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天衍凰妃:凤逆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天绝山脉的宋局长)的经典小说:《天衍凰妃:凤逆天下》最新...
- 15723058字12-26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811279字07-03
- 独步成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搞个锤子)的经典小说:《独步成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5353342字07-05
- 魔王大人,勇者他又招了
- 909747字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