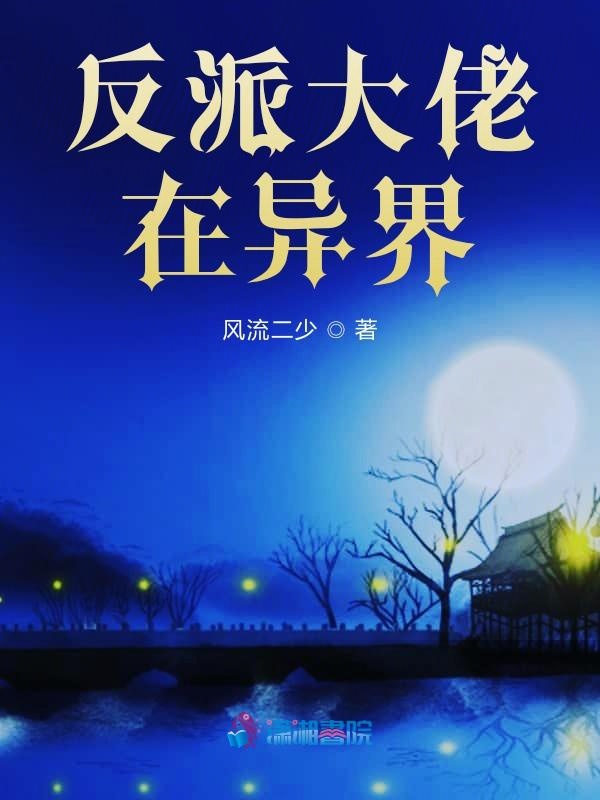第370章 考官篇(四)
祸,言辞激烈却空洞无物;要么是盲目鼓吹开海通商,描绘黄金万两流入的美梦,却对如何应对倭寇、管理贸易、平衡财政等实际问题避而不谈,或言之无物。
真正能客观分析利弊、提出切实可行方略者,寥寥无几。
“百无一用是书生,此言……”陈恪心中暗叹,后半句咽了回去,只是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强打精神继续批阅。
就在这时,一个带着几分刻意炫耀的声音在陈恪案边响起:“靖海伯初次阅卷,想必劳神。本官倒有些心得,这判卷呐,首重立意,次看文采,最后才是经义贴切与否。尤其这策论,须得……”
赵文华踱步过来,脸上堆着“前辈”式的笑容,显然是想抓住这个陈恪“不懂”的领域,好好秀一把资历。
陈恪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没听见他的话,目光专注地落在新一份朱卷的起首几行。
他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案几,示意旁边侍立的书吏将下一份未取卷递过来。
动作自然流畅,完全无视了赵文华的存在和即将开始的“教诲”。
赵文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如同被冻住的猪油。
他张着嘴,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周围的几位考官都注意到了这无声的尴尬,有人低头装作看卷,有人嘴角微微抽动。
赵文华老脸一红,最终只得冷哼一声,讪讪地踱回自己的座位,那背影僵硬得如同生锈的铁板。
陈恪根本不在意身后那道怨毒的目光。他的心神已被手中的新卷吸引。
这份策论开头便与众不同。
它没有急于站队抨击或鼓吹海禁,而是如同一位沉稳的史家,从上古“市易有无”讲起,历数商周、秦汉、隋唐、宋元的海路贸易兴衰,条分缕析地阐述开放与封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弊得失。
论据扎实,文气平和,逻辑清晰。
最后,文章竟以极其标准的“颂圣”结尾:“伏惟陛下天纵圣明,洞察幽微,于海疆之策,自有乾纲独断。臣等惟恪遵圣谕,竭诚效力而已。”
陈恪的嘴角,难以抑制地向上扬起。
这手法……太熟悉了!
这不正是他当年中举时写《盐铁论》策论的翻版吗?
只不过此人比他当年更加圆融、更加稳妥,那份锐利的锋芒被厚重的史料包裹,最终以恭谨的马屁完美收束,堪称考场“保命”与“展才”的典范。
“好一个‘述而不作’!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