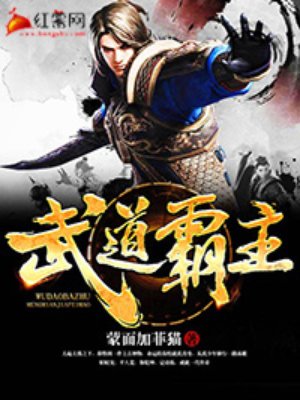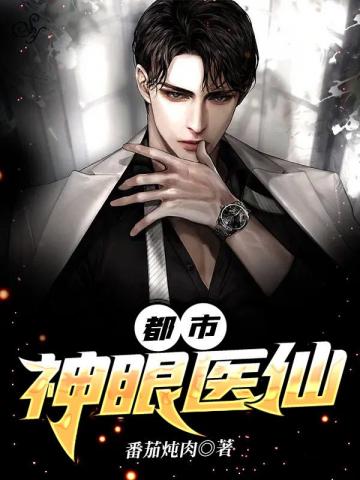第332集:《沙漠中的苗医站》
,穿百褶裙的妇人背着竹篓从诊室门口经过,篓子里的草药叶片上还挂着露珠。
“下周这个时间再复诊。”李医师在电子处方上勾选药材,“我开的‘祛湿茶方’会从贵阳保税仓寄给你,清炒过的薏米配茯苓,比生薏米更不伤胃。”系统自动弹出英文说明,标注着服用禁忌和海关通关需要的文件。
结束诊疗时,陈佩雯发现通话时长显示47分钟。比她去社区医院排队两小时、问诊五分钟要高效得多。更意外的是诊疗费,换算成美元只有医保自付部分的三分之一。
她起身去厨房倒水,路过客厅时瞥见儿子贴在冰箱上的涂鸦——画里有个戴银项圈的医生,正用放大镜给地球看病。六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苗医,只知道妈妈今天没像往常那样抱着头皱眉。
贵阳的诊疗中心里,李医师刚结束当天最后一场远程问诊。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玻璃柜里陈列的银质药碾子在暮色里泛着柔光。墙上的电子屏实时更新着全球接诊数据:纽约37例,伦敦29例,悉尼18例,还有新加波的一位患者特意留言,说按指导用榴莲壳煮水熏蒸,多年的关节痛居然减轻了。
“李老师,肯尼亚那边有个患者对‘隔姜灸’的姜片厚度有疑问。”年轻医师小杨拿着平板跑过来,屏幕上是位黑人妇女的手,指关节明显肿大。李医师凑近看了看,用当地斯瓦希里语的音译回复:“用姆瓦伊(生姜)切得像手机卡那么厚就行,要带皮的。”
窗外的苗寨渐渐亮起灯火,鼓楼顶端的铜鼓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李医师想起三年前跟着师父上山采药的情景,那时师父说:“苗医的根在这山里,但药香要能飘到山外才算本事。”现在,那些曾被装在竹筒里、用蜡封好送给远亲的草药方子,正通过光纤信号传到七大洲去。
陈佩雯收到快递是在五天后。包装盒子上印着苗绣纹样,里面除了分包好的草药,还有一张手绘的明信片。李医师用毛笔写着:“纽约的湿气重,雨天记得把茯苓片放在衣柜里。”背面画着简易的穴位图,旁边歪歪扭扭地签着个苗文名字。
她把明信片贴在冰箱上,和儿子的涂鸦并排在一起。那天晚上,她按照视频里教的方法,用砂锅煮了祛湿茶。药香弥漫开来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这个住了五年的公寓,第一次有了家的味道。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技术团队的办公室里,小张打了个哈欠。监控屏上,全球在线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三千。林教授正对着麦克风说:“把‘蛊毒’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上都城来了个狐狸精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赢香)的经典小说:《上都城来了个狐狸精》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627697字10-29
- 开局抱上魔尊大腿,开启摆烂人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湘侞)的经典小说:《开局抱上魔尊大腿,开启摆烂人生》最新章...
- 1316443字03-12
- 武道霸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蒙面加菲猫)的经典小说:《武道霸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0357703字04-27
- 都市神眼医仙
- 我是老中医,专治各种吹牛逼!我武道超神,吊打一切不服气!秦飞偶得神秘传承,拥有神...
- 8341756字10-16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